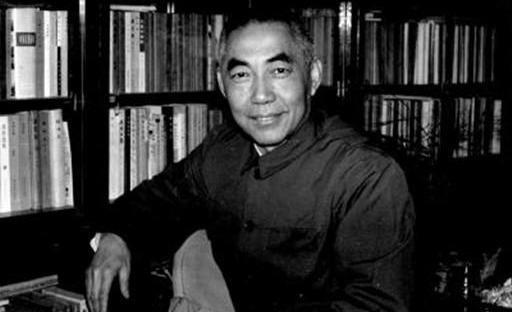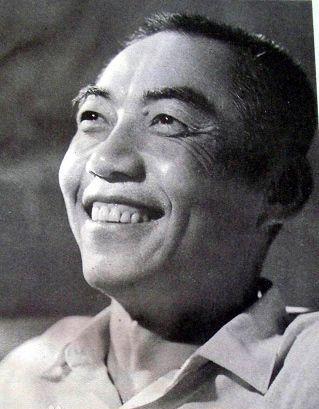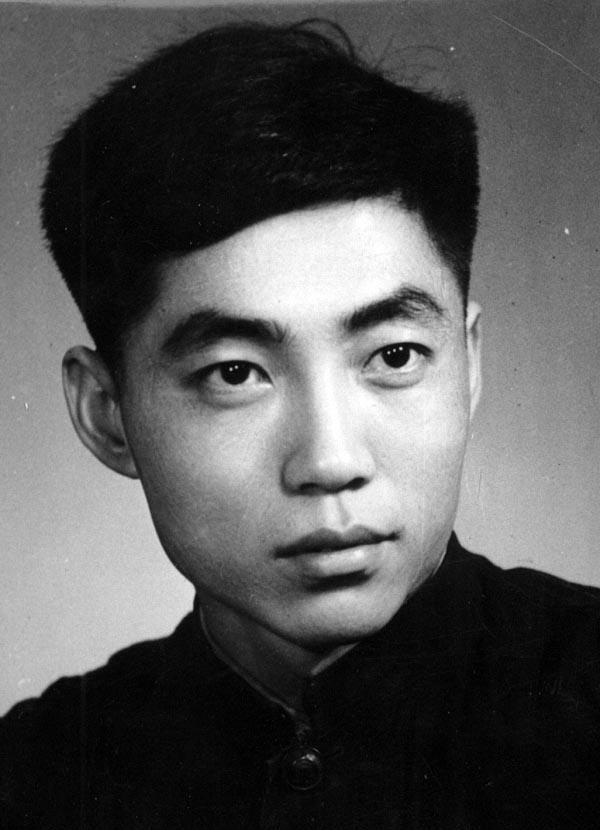当我们拿起那把名为“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评估体系”的尺子——这把尺子量的是作品的内涵深度、人物形象刻画、阅读趣味、艺术表现力以及它留下的影响痕迹——去仔细衡量浩然在个特殊时期写下的长篇小说,特别是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这一路,会发现事情并不像有些人极力鼓吹的那样美妙。 先说最核心的内涵。这是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根基牢不牢靠的关键。浩然这两部大书,讲的核心是什么?是农村里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围绕着走哪条路的路线分歧。作者笔下,这种斗争尖锐得无处不在,激烈得仿佛随时要天翻地覆。然而,回头看看那段真实发生的农村历史,不得不承认,书里描绘的那种斗争场景,很大程度上是被夸大其词了,甚至有些地方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情节。 有人说,《金光大道》必然有其永远屹立于艺术殿堂的理由。这话听起来很提气,但细究起来,更像是拔得太高、说得太满的空话,实在找不出足够硬气的理由来支撑。试想,如果《金光大道》这样的作品都能稳稳占据艺术殿堂的一席之地,那这个殿堂本身的价值和门槛,恐怕就很值得怀疑了。不光《金光大道》算不上经典,就连评价相对好些的《艳阳天》,同样也难以戴上经典的桂冠,尽管不少人认为它在艺术上比《金光大道》要强一些。归根结底,从长远来看,读者手中那无形的投票权,最终会让《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成为历史书架上的旧籍,它们的时代已经过去。 再来谈谈作品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真实是文学打动人心、长久流传的生命线。浩然本人曾多次强调,他写的就是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是他认为的真实状况,绝无虚假。这个说法本身就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他后来也曾私下对采访者吐露过心声:“农民的苦处,我哪里会不知道?我就是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农民娃,他们的日子、他们的难处、他们的怨气,我太清楚了。那几年大家挨饿受冻的日子,我不是一样熬过来的吗?可是,这些话,那时候能往书里写吗?不行啊!写了也出不来!” 这段自白本身就充满矛盾,也戳破了他之前宣称的“完全真实”的泡泡。既然明明看见了、经历了苦难,却不敢在笔下讲真话、说实话,那么作为一个握笔的作家,他的良知和勇气又体现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无论时代如何,都是值得认真反思,甚至应当感到愧疚的。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如果真的如实写下农民挨饿受冻的惨状、心中的怨气和生活的绝望,那么《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样基调昂扬、歌颂奋斗的作品,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诞生。 那么,这些小说读起来有趣吗?换句话说,它们的趣味性如何?这关乎读者能否顺畅地读下去并获得阅读的愉悦。实事求是地说,浩然在文革期间写的这些小说,并非依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或独特的艺术魅力来吸引读者的。尽管浩然扎根农村多年,深知农民想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作品里也大量运用了鲜活生动的农民口语,充满了泥土气息和生活的细节,这使得他的书在当时确实拥有不少读者,尤其是一些农民朋友。 他后来回忆起1962年这个创作转折点时曾说:“那会儿我已经出了好几本小说集了,很想再往上走一步,把作品质量提得更高,可就是找不到明确的路子。就在这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伟大的号召,简直像春雷一样劈开了我脑子里的迷雾!” 这话很清楚地表明,他寻求突破的方向并非更深地扎根生活、磨砺写作技巧或提升个人思想境界,而是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强大的理念作为支撑。这个选择,直接决定了他作品的基调:注定要紧跟瞬息万变的政治风向,注定要走歌颂路线,也注定了作品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说教色彩,成为某种政策或理念的形象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