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药明康德
达伊扎·戈登(DaizaGordon)的人生两度被命运重创。她的两个弟弟先后因罕见的亨特综合征(Huntersyndrome)夭折,她亲手为最小的弟弟做心肺复苏,却仍无力回天。多年后,轮回再现——她的三个儿子也被确诊为同样的疾病。那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冰冷的病房,只不过,这一次她是母亲,心碎加倍。
亨特综合征本是一道无法逆转的判决:患者因缺少IDS酶而逐渐丧失语言、运动与听力。然而,如今科学正带来希望。戈登的孩子们参加一项突破性的临床试验,通过“脑穿梭系统”将IDS酶穿越血脑屏障送入大脑。两个年长儿子重新听见声音、自由奔跑,年仅两岁的幼子接受治疗后更几乎无症状。这是科学与命运的一次较量,让她首次敢于期待与孩子们共享未来。
这一切改变,源于科学家逐渐突破了曾经难以逾越的医学屏障——血脑屏障(blood–brainbarrier,BBB)。

处于“封锁区”中的大脑
人类大脑漂浮在脑脊液中,是一种极为“挑剔”的器官。它由约650公里长的血管供养,血管内层由致密排列的内皮细胞组成,构建成一道天然防线——血脑屏障。这一屏障拒绝绝大多数有毒分子通行,仅允许氧气、葡萄糖等必要营养物质通过。而多数传统药物,尤其是大分子生物药(如抗体、酶、基因载体),都难以穿越这道屏障。
过去,为了让药物进入大脑,研发者通常选择体积小、脂溶性强的合成分子,例如帕金森病药物左旋多巴(levodopa),可“搭便车”借助氨基酸转运蛋白进入脑部。但对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罕见病或脑转移癌等疾病所需的大分子药物而言,仅约有0.1%的注射剂量药物能够进入大脑,因此除了导致大量药物的浪费外,高剂量药物的注射也增加患者的不良反应,因此长期以来相关药物的开发便迟滞不前。
脑穿梭技术的诞生
为了攻克血脑屏障这一长期阻碍脑部疾病治疗的技术难题,科学家开始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能否模拟大脑自身的运输机制,把药物“伪装”成大脑愿意接收的物质?于是,“脑穿梭技术”应运而生。这项技术的核心理念,是借助天然的受体介导转运机制,把难以穿透血脑屏障的大分子药物送入大脑。
目前最为成熟和广泛使用的方法,是基于转铁蛋白受体(TfR)。这种受体天然存在于脑血管内皮细胞上,负责将结合了铁元素的转铁蛋白(transferrin)从血液中带入脑部,是大脑获取铁的重要通道。研究人员利用蛋白工程技术,将治疗性生物大分子(如抗体、酶、核酸或病毒载体)与能够识别并结合TfR的“穿梭模块”连接,使整个复合物可以“搭便车”通过这一通道被脑血管内皮细胞吞噬,随后穿越细胞并被释放至大脑内部,从而实现高效、定向的脑部递送。研究显示,在引入“脑穿梭系统”后,静脉注射药物进入大脑的比例得到数量级的提升。

该技术已经在多个重要项目中取得突破性进展。2021年,JCRPharmaceuticals推出的JR-141酶替代疗法,成功利用穿梭系统将IDS酶送入大脑,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的脑穿梭药物,目前已在日本上市用于治疗亨特综合征。而戈登孩子所参与的研究项目,则由DenaliTherapeutics主导,其研发的穿梭式酶替代疗法也被美国FDA授予快速通道资格。
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的适应症远不限于罕见病。在阿尔茨海默病领域,罗氏(Roche)开发的trontinemab是一款在原有抗体基础上添加穿梭模块的新型药物,初步临床数据显示:在剂量减少五分之四的前提下,其清除脑内淀粉样蛋白的速度提升了三倍,且脑水肿等不良反应显著减少,为神经退行性疾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目前,多个相关研发管线正在扩展至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例如神经代谢障碍、帕金森病、脑部转移癌、肌萎缩侧索硬化(ALS)等。
下一代技术的加速演进
此外,研究人员在不断优化基于转铁蛋白受体的第一代脑穿梭系统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其他天然血脑屏障转运机制,以期实现更广谱、更精准的大脑药物递送。其中,几种新兴“穿梭载体”正在逐步展现出巨大潜力。
例如,CD98hc蛋白是近年受到广泛关注的转运靶点,它是一个跨膜蛋白复合物,天然参与大脑中氨基酸和肽类物质的转运。与转铁蛋白受体相比,CD98hc的转运速度更慢,但其特殊的定位机制可能更适合用于治疗细胞外病理靶点。DenaliTherapeutics等公司已在相关方向投入大量研究资源,试图优化CD98hc为基础的穿梭平台。
在病毒载体系统方面,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BenDeverman教授团队成功对腺相关病毒(AAV)外壳进行了结构改造,使其具备识别转铁蛋白受体的能力。这一改造使病毒能够高效穿越血脑屏障,并将目标基因传送至脑细胞。在动物实验中,该技术已能实现对罕见脑部代谢病的基因替代治疗,具有一次治疗即可产生持久效果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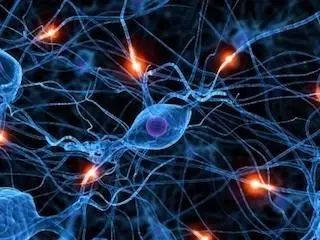
与此同时,外泌体(exosomes)作为天然的细胞间信使,也逐渐成为神经递送工具的明星候选。牛津大学的RNA生物学家MatthewWood教授团队将识别TfR的抗体嵌入至外泌体表面,并尝试将其作为CRISPR–Cas9等基因编辑系统的递送平台。由于外泌体本身即具有运输蛋白质和核酸的天然能力,加之免疫原性低、生物相容性好,具有成为下一代脑部药物关键载体的潜力。
不仅载体形式日益多样,所递送的“货物”也逐渐从蛋白质拓展到RNA和DNA类治疗手段。2024年,科学家在小鼠与猕猴大脑中,首次通过TfR结合分子将寡核苷酸成功跨越血脑屏障,并实质性降低了目标致病蛋白的表达。这一成果标志着RNA干扰药物在神经疾病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产业回潮,创新再启航
回顾过去,中枢神经系统(CNS)药物研发曾因失败率高、作用机制模糊,使众多医药公司“望而却步”。然而,随着脑科学基础的积累、成像技术与生物标志物的进步,以及脑穿梭技术的涌现,整个领域迎来逆转。过去六年间,资本和药企纷纷回流CNS赛道,尤其通过对小型神经生物技术公司的数十亿美元收购与合作,推动行业快速扩张。
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得益于脑穿梭技术的发展,全球CNS药物研发管线增长超过30%。更令人瞩目的是,其中约四分之一为需借助穿梭系统的大分子生物制品,这不仅代表着临床需求的巨大转变,也预示着未来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脑癌、神经遗传病等难治性疾病的全新方向正在逐步成型。

脑部穿梭技术,正逐渐从科研实验走向临床现实。从戈登的家庭,到全球数以百万计受困于罕见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脑癌患者的家庭,这项技术带来的不只是新疗法,更是对未来的全新定义。
“我知道临床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戈登说,“但看到孩子们的改变,我终于敢去想象我们能一起走得更远。”
参考资料:
[1]Breakingdownbarriersinbrain-drugresearch.RetrievedMay31,2025from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1569-z
(转自:药明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