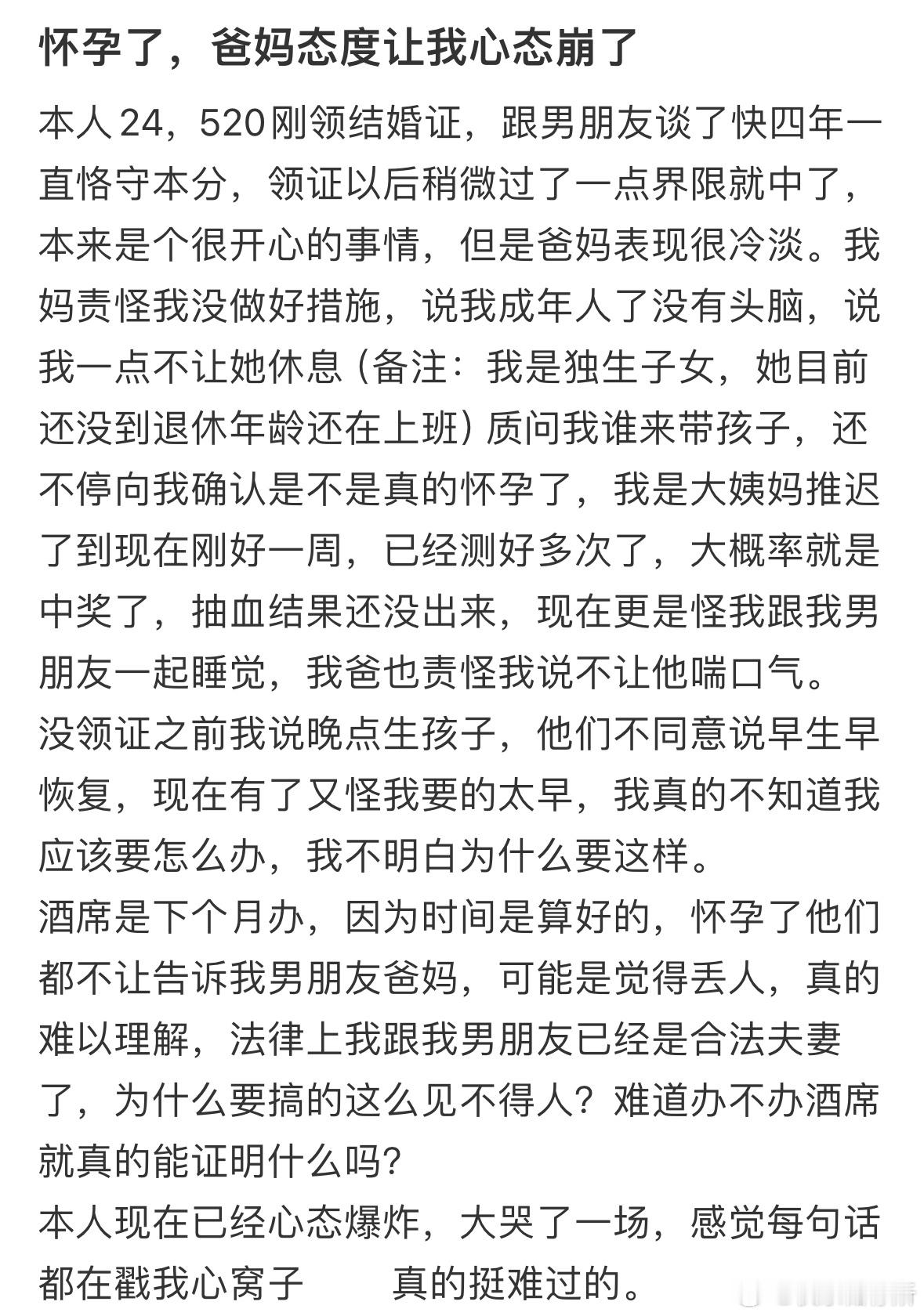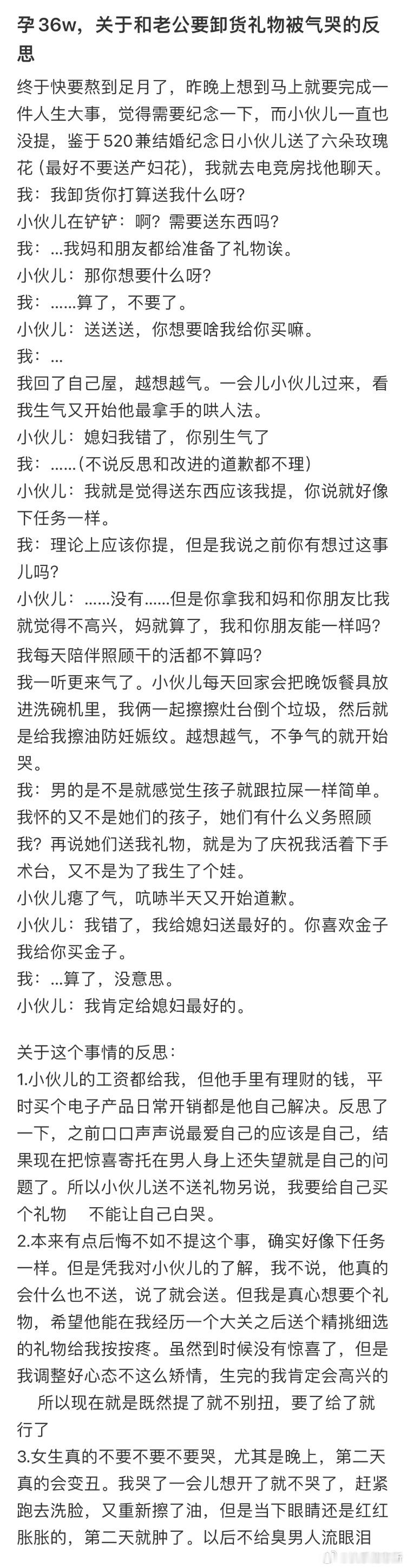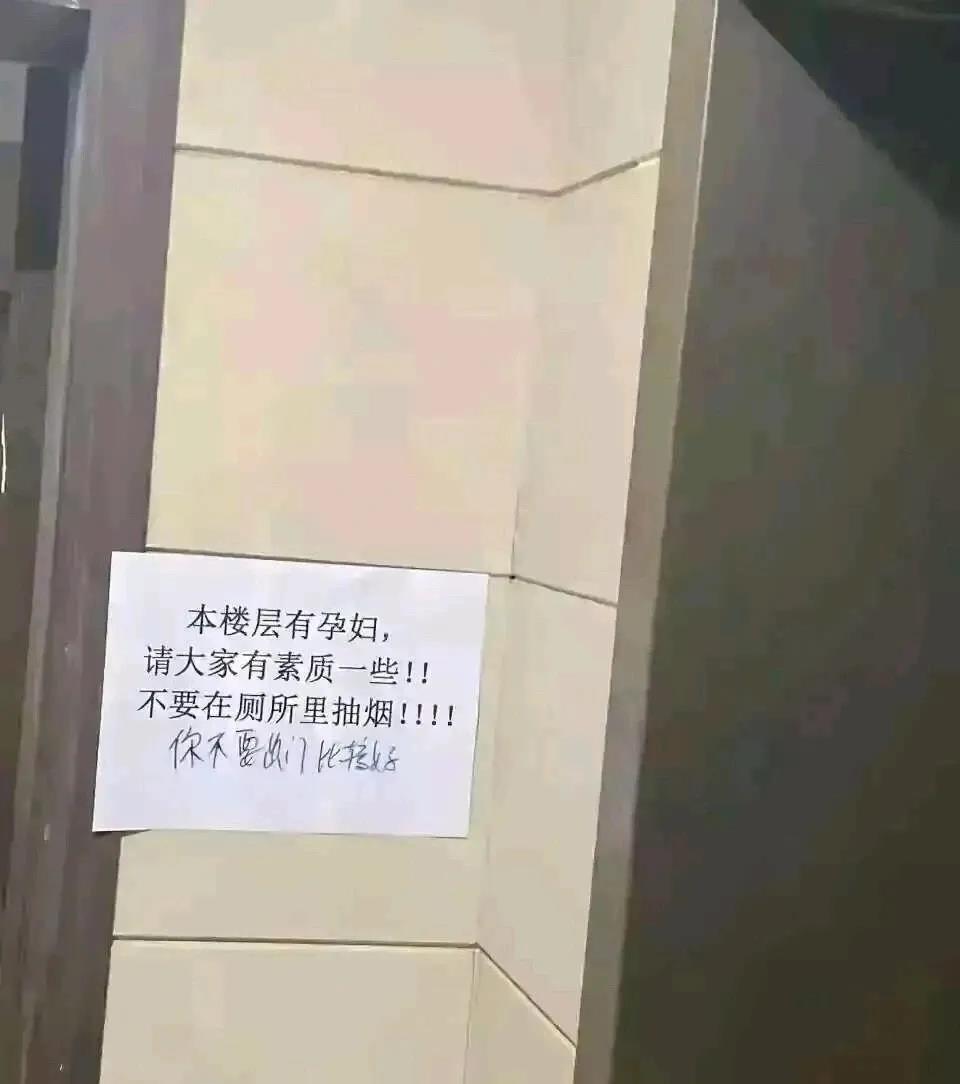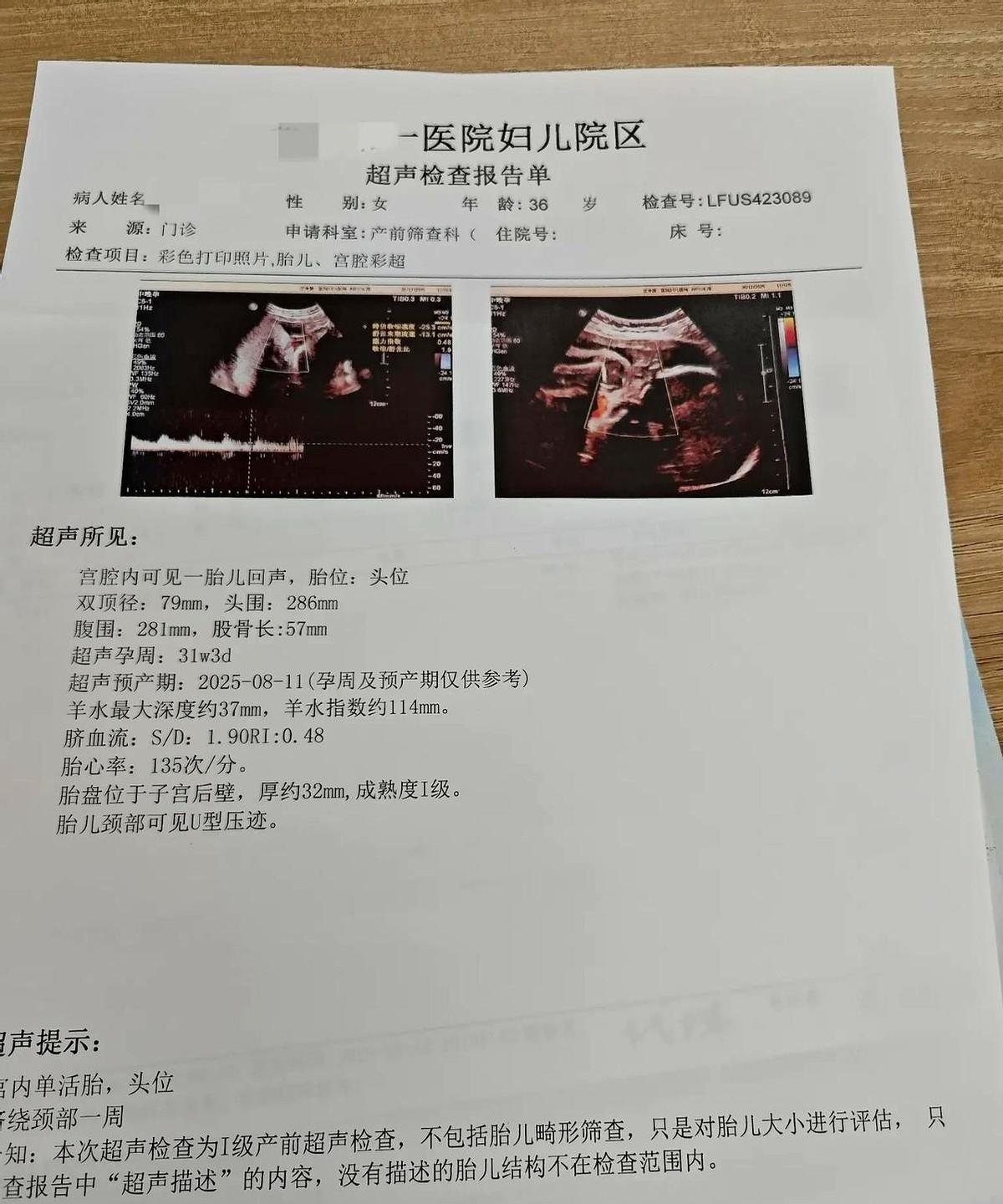1943年,一位产妇在山沟里承受着分娩的剧痛,在痛到几乎昏厥之际,她死死攥住母亲的手。可当婴儿呱呱坠地后,她竟猛然将孩子推开,咬牙切齿道:"就算天打雷劈,我也绝不认这个孩子!" 【消息源自:山西省档案馆《盂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调查》;东京女子大学《中国华北地区慰安所分布研究》(2015);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幸存者口述史汇编》】 曹黑毛蹲在灶台前添柴火时,听见村口传来第一声狗叫。那年她刚满十八,身上还穿着母亲用攒了三年的布票换来的红棉袄——原本是预备当嫁衣的。"妮子快跑!"母亲突然冲进来,手里攥着把接生用的剪刀,指甲缝里还沾着昨天帮邻居家媳妇催产的羊水腥气。 脚步声比枪声先到。三个戴屁帘帽的日本兵踹开木门时,曹黑毛正把剪刀藏进裤腰。领头的少尉靴子锃亮,刺刀挑起了她的下巴:"花姑娘,好。"母亲扑上来咬住那人手腕,被枪托砸中太阳穴的闷响,像极了曹黑毛昨天在河边捶打湿衣服的声音。 千口村的晒谷场成了临时据点。二十多个姑娘被铁丝圈在碾盘周围,有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医挨个检查牙齿和骨盆。曹黑毛听见隔壁春燕在哭:"俺定过亲了啊..."话音未落就挨了耳光,血珠子溅在去年新刷的"丰"字照壁上。那天傍晚,她们被卡车拉进县城澡堂,肥皂沫混着消毒水灌进鼻腔时,曹黑毛突然想起未婚夫王家小子说过要带她去太原看火车。 慰安所的木板房透着风,曹黑毛数着屋顶裂缝熬过第一个月。每天天不亮,门外就响起皮靴跺脚的队列声。"佐藤少尉说要特殊照顾你。"翻译官扔来盒雪花膏时,她正用草纸堵住经血——昨天被三十七个兵折腾到后半夜。最难受的不是疼,是那些兵完事后总爱用刺刀划她肚皮,冰凉的刀刃贴着肚皮游走,像在检验牲口膘情。 第二年开春,曹黑毛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偷偷观察过,佐藤的勤务兵总在周三午休时打盹。那天她灌下三碗井水,抡起石杵夯了整上午军服,直到裤脚渗出血浆。昏迷前最后的记忆,是母亲教过的口诀:"见红就揉合谷穴..."但这次她故意反着来,指甲深深掐进小腹的旧伤疤。 逃亡那晚下着瓢泼大雨。曹黑毛撬开后窗铁栅时,听见哨兵在哼《樱花谣》。她光脚蹚过雷公河,泥浆里泡着的避孕套像极了王家提亲时送的玻璃糖纸。躲进狐子岭的山洞第三天,胎动突然变得剧烈,她摸到胯骨突出的形状——去年被军马踢过的地方已经变形。当羊水混着血块冲出来时,曹黑毛抓起接生的剪刀,这次对准的是婴儿的脐带。 战后第七年,同村的退伍残疾军人来提亲。那汉子少条胳膊,但会帮她煎治疗盆腔炎的药草。有次曹黑毛发病说胡话,把药罐当成了日本兵的饭盒砸碎,男人只是默默扫净碎片:"咱都知道,不怨你。"1995年去东京作证前夜,七十三岁的曹黑毛突然翻出那件红棉袄,发现剪刀锈出的黄渍早已盖过了当年的血迹。在法庭上,当日本律师质问"如何证明孩子是日军骨肉"时,她解开裤带露出盆骨的凹陷:"这够不够?" 去年清明,千口村后山的歪脖子枣树下多了块小石碑。曹黑毛的养女蹲在那儿烧纸钱,火苗舔过"无名氏"三个字时,山风里恍惚传来婴儿啼哭。养女回头问要不要加件衣裳,老人摆摆手,把助听器音量调大——里面正重播着外交部谴责日本歪曲历史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