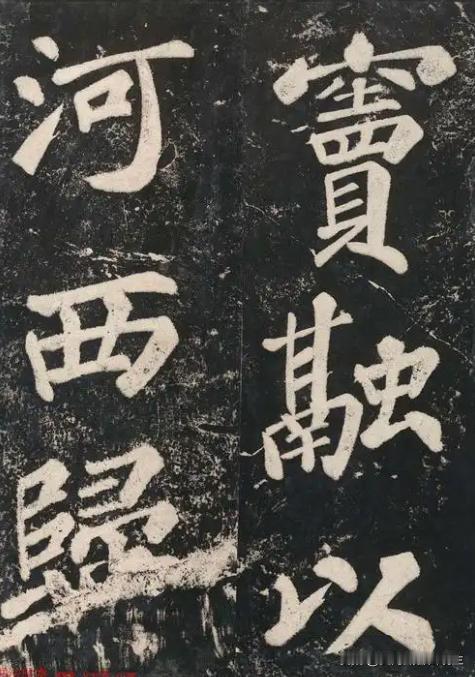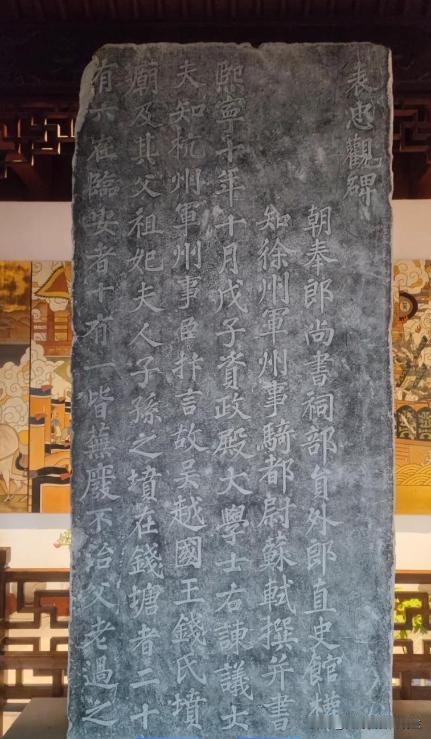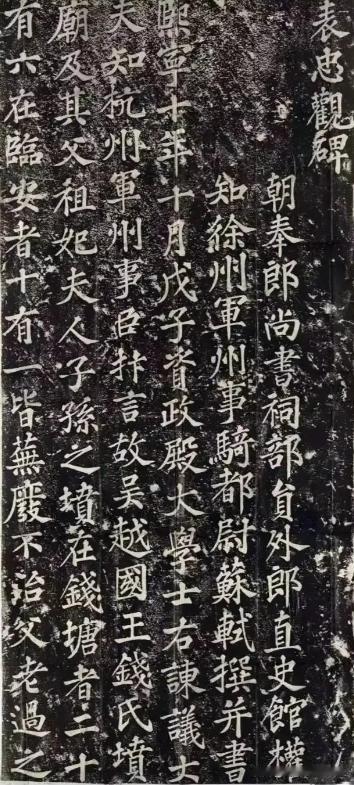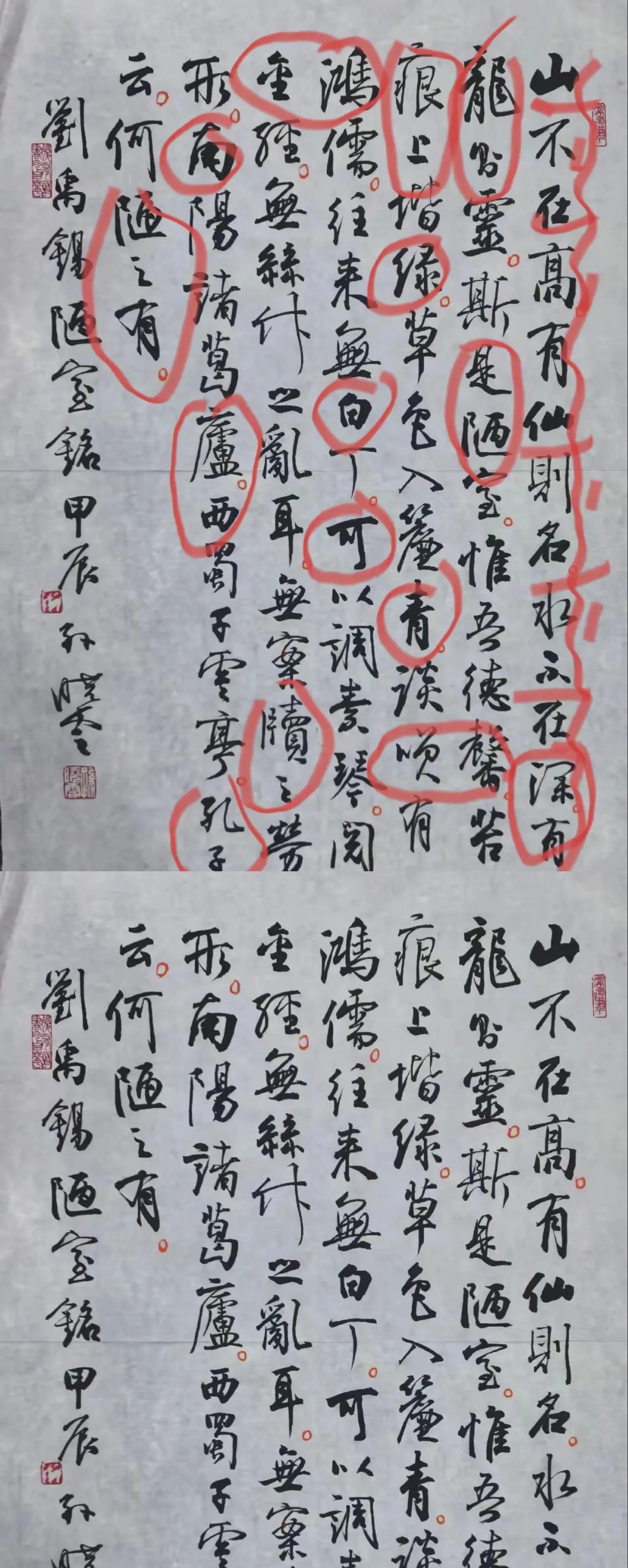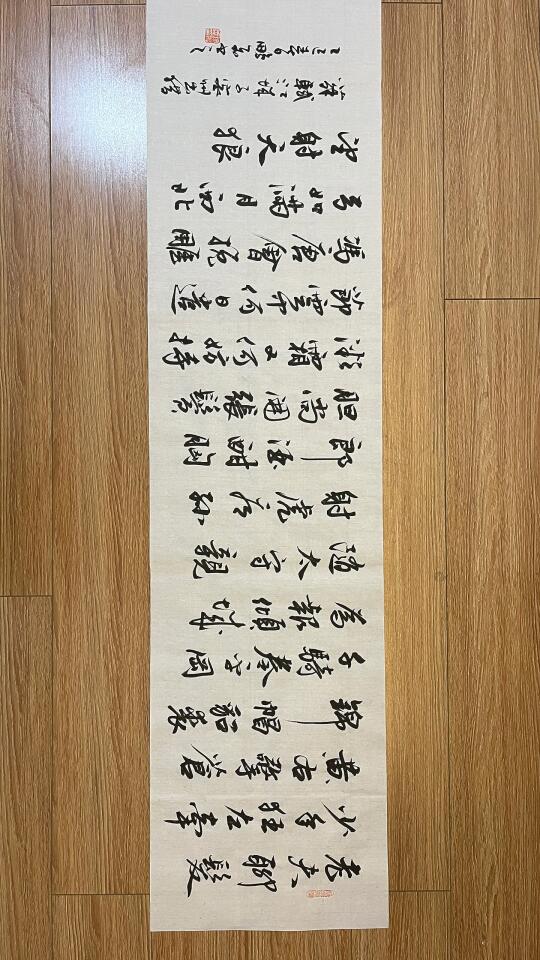清代碑派书法史观如何完成建构与嬗变? 书法史观体现了书法史家对于书法艺术历史发展的一种认识和看法。 而碑学的兴起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碑学史家之所以形成迴异于前代书史家对书史的阐释。 原因在于碑学史家所具有的独特书史观,碑派书史观的建构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清代前期冯班、陈奕禧、杨宾、何焯等书史家对于书史的阐释,不难发现已有了碑派史观的萌芽。 而清中期阮元、包世臣等人的书史观则明显不同于前人,有着十分显著的碑学特色;晚清康有为以“尊碑卑帖”著称,可谓是碑学之激进,其书史观的碑学色彩也最为浓烈; 其他晚清史家如杨守敬、梁启超等人,虽未一味“尊碑”,但他们的书史观也显然有着“碑派”意味。 即便如刘熙载也没有摆脱“碑派”影子。 碑派书史观较之于之前书史观的最大不同则在于将书史脉络由“一元”拓展为“二元”在帖学传统之外,寻绎出一条碑学源流。 碑学史家对于书法史的认识也不再局限于精英史--书家史,而使更多的非名家书迹,甚至是无名书迹进入了史的视野。 客观而言碑派书史观在清代的建构与发展,对于认识书法发展历史,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书法艺术的传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同时伴随着这一史观的逐步被认同,不仅改变了人们既往的书史认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书法艺术自身的认识和评价,为书法艺术的发展特别是碑派书法的发展起到了无以替代的作用。 当然,就碑派史观而言,其不仅存在着一些理论自身上的难以自圆其说,同时,考之于史也存在着观念与史实不符的问题,另外,破除“精英”崇拜、推崇“民间书法”所导致的“书法泛化”的弊端也不可不视。 清代碑学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沈语冰曾言碑学“引起了中国书法从基本技法到创作思想,从创作思想到趣味好尚,从趣味好尚到艺术理念的全方位、整体性的变革”。 白谦慎认为近三百年来,碑学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并将碑学于中国书史之地位譬之印象派绘画于西方艺术史之地位,可谓一语道破清代碑学的研究意义和重要价值。 早在上个世纪,就出现了许多关于清代碑学的讨论,朱大可在《论书斥包安吴康长素》一文中,批评了包慎伯和康南海的碑学理论。 特别是反对他们“尊魏卑唐”的学说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就清代碑学与帖学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对清代碑学所存在问题进行了委婉的批评,白蕉则站在帖学立场对包慎伯、康南海的碑学理论提出了批驳。 他在《碑与帖》中认为包、康二人的治学态度显得不负责任,学术观点也有失偏颇,白氏评价此二人善用自己的想法测揣度真正的书法史,这是不可信也不可取的。 应一成与白蕉相同,是站在帖学的立场批评碑学理论,在其《碑学与帖学》中认为碑学理论家有“自视甚高”、鄙视和故意诋毁帖学之嫌疑,清史专家戴逸则对帖学与碑学持客观。 调和的态度,其认为“南帖派”与“北碑派”二者各有优劣,碑派学者在立论基础上抓住了帖学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问题,这本无可厚非。 奈何碑派学者不能持相对客观的态度处理碑学与帖学的关系,“贬斥异己,一笔摸杀”是极为不可取的治史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