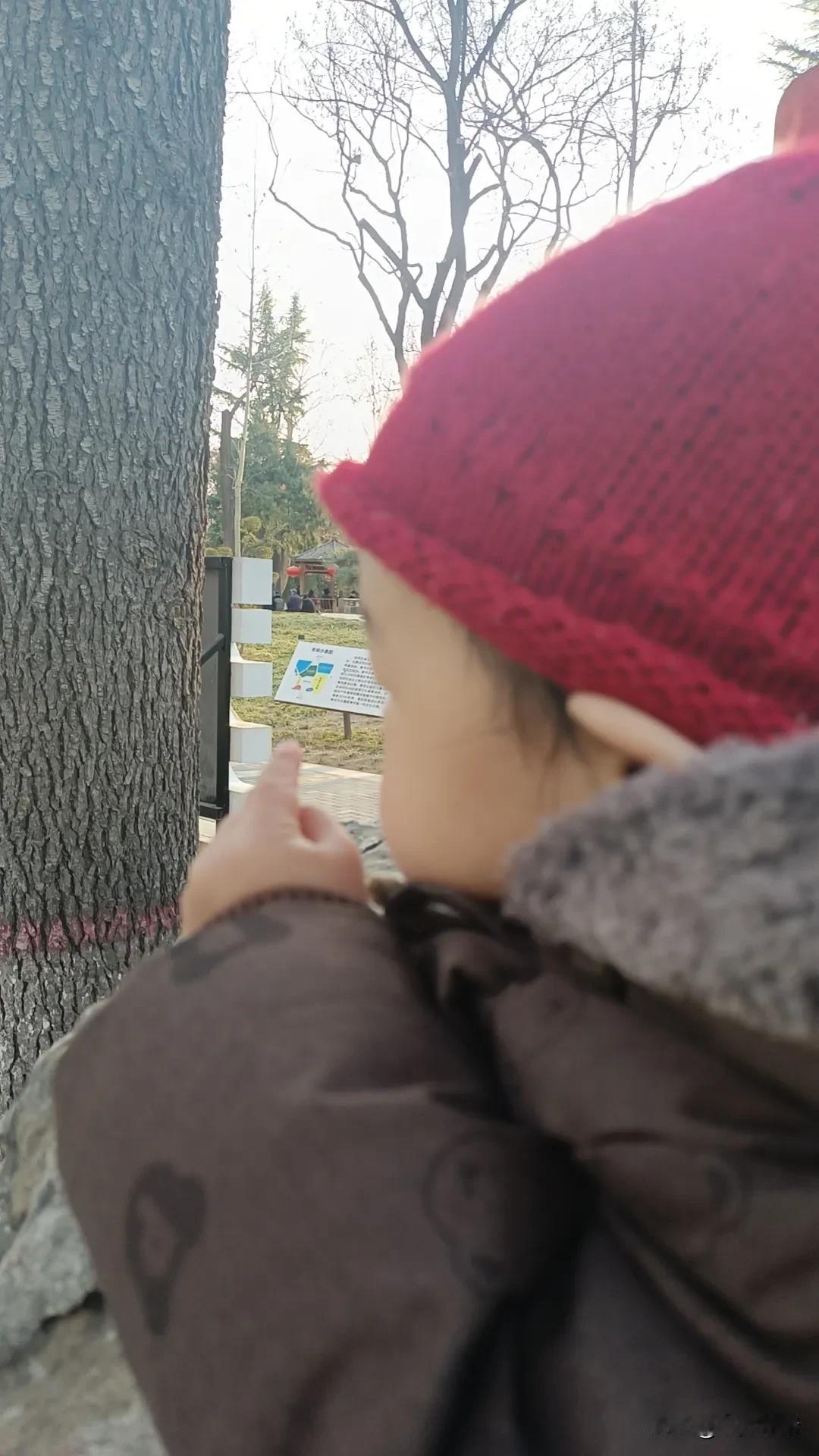带孩子会有很多貌似无意义的时间段落,不知道孩子的小脑瓜儿在想什么,她为何要对着空荡荡的眼前世界凝望,为何一再对同一个景色、同一种石头子、小树叶之类的东西怎么看也看不够?如果你先否定了她对眼前你熟视无睹的世界进行长时间凝视的意义,那自然就只剩下了纯粹消耗时间的无意义无价值感了。 这时候需要耐心地以她的视角去看眼前的世界,对她凝望的你以为不值得凝望的一切也试着凝望一会儿,往往就会发现即便不是以孩子的学习成长角度来看,也还真的是有其凝望价值。就像在画展的时候看一幅画,画家之所以画这个场面一定也是长时间凝望与深陷于浮想联翩的结果。 一片水,水中有防腐木铺成的桥,桥故意不走直线而走曲径通幽的曲线,为的是多造几个景;桥上拴着的救生圈有白色的有橘红色的,都很醒目,都很轻,系在栏杆上的绳子都是活扣儿,一拽就开,假如有人落水的话,一定不能摘下来就甩过去,一定要跑过去,跑到最靠近落水者的岸边,确保能将救生圈甩到落水者能抓到的位置上…… 好不容易走过这一片水面了,也许用了二十分钟,也许是四十分钟。之所以离开,是因为突然发现对岸有健身路径的各种器械。每一种器械都要逐一去实验一下,能晃动的就站上去晃一晃,能起伏的就坐上去起伏起伏,这一下就又是二十分钟或者四十分钟。 带孩子先就有了绝对的耐心,否则是无法完成任务的。实际上只有出于爱、出于陪伴婴儿成长的真诚意愿才能让一个成年人一直这样亦步亦趋地带孩子。有了耐心,心甘情愿地以孩子的兴致、速度和节奏为准绳,才对孩子和大人都好。 婴儿个子小,视角低,视野有限,所以看到更多的是细小的事物,是事物的细节,落叶啊,蚂蚁啊,小石子啊,尘埃啊,草茎啊什么的。这当然也更是因为心智尚在发育,对于广大的地理和宏伟事物的把握能力非常有限。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其发现高远的事物,比如月亮,比如天空中画出一道白线的飞机,比如风筝和热电厂的烟囱。毕竟婴儿拥有人的一生中最好的、一尘不染的视力,拥有对万事万物一丝不苟、兴趣盎然的专注力。认知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事物,就是这个年龄段乐此不疲的人生内容的全部。 即使去同一个公园,每次去,婴儿也都像是第一次一样新鲜,总是能发现好像以前没有发现过的物象。当然其中一定有以前熟悉的路径,熟悉的角度,更多的却一定是一下就能玩上很长时间的新发现。在这样的新发现面前,以前非常感兴趣的东西也许还要复习一下,但明显是对崭新的东西更愿意多关注。 花开了,麻雀起落,小草有了绿意,喷灌转着圈喷水,亡羊补牢的雕塑上羊的另一只角也断了,不锈钢质地的大型雕塑基座位置上有一个可以打一下滑梯的地方,跑到老飞机下面晃动翅膀上的调节扇的大孩子的动作声响很大,向她打招呼的一个小姐姐面对她只知道望着人家而始终面无表情的状态依旧打着招呼的热情或者说是好奇…… 随着婴儿的眼光看着熟悉得再熟悉不过的公园,只有缺少行动能力走不远的老人才愿意一来再来的公园,就会惊喜地发现,方寸之地也常有常新,只要放低身段,降低视角,就一定会有崭新的意趣。 她坐在至少是现阶段最喜欢的秋千椅上荡啊荡,很快就睡着了。一睡就睡了一个小时,醒来以后发现还在秋千椅上,立刻就又开始荡了起来。指着我身后的包嗯嗯了几声,意思是让我给她从里面拿点吃的。一边吃一边荡秋千,那才惬意呢。一直荡到她不愿意再在秋千椅上待着了,这才下来。连睡觉在内累计在秋千上待了俩小时。 这是婴儿的时间使用方式。婴儿眼中的时空可能是模糊的,也可能是比成年人清晰真切得多的。她一定会忘记时间的存在,甚至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她的人生滋蔓着将时间裹挟在内,完全以自己所见的世界为主导,以自己不自知的内在需要为主导,不以这两者之外属于成年人的维度观念的时间为主导。那一定是一种缤纷摇曳的梦幻人生状态,看孩子的大人是人类成年以后与这种状态形成的最为贴近的时刻。 婴儿没有时间,婴儿甚至也不会记得场景,但是会记住被陪伴、被爱的温暖。婴儿以自己的手无缚鸡之力状态而完全依赖于父母和成年人,是其自身成长阶段决定的身体状态,也是在情感上引起成年人无私的爱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不是有意为之,但客观上是绝对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男女老幼都会对婴儿充满了爱惜之情,哪怕是自己脱离开婴儿状态还没有几年的小孩子,比如那个在遇到的时候一直在和婴儿打招呼的小姐姐。 以前一直认为时间是线性的,音乐是时间艺术;和婴儿在一起,和婴儿一起走到户外就会发现,和音乐同时也是空间艺术一样,时间其实也是空间状态的存在,是大自然的气氛美学的构件。婴儿天然地拥有这样的感受力,同时表现在对时空的认知和使用上的无知无觉和敏感灵透。 这样带着婴儿出来玩就会有一种自己重新走进世界的玄幻感,就不会觉着漫长乏味,就会对婴儿充满了感恩:她刷新了你的麻木、引领了你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