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讲究雷厉风行。但雷厉风行这种工作方法是有局限的。在对同志,对复杂的情况下,雷厉风行就转化为一种急躁。---这一点,彭总自己也认同的。庐山会议,他原本想和毛主席谈话,但后来想他和毛主席都是急性子,怕说着说着,就吵起来,所以就写信了。黄克诚上山后,彭德怀把自己写给毛主席的信给他看。黄克诚读后说:“信中的意见我赞成,但写信的方式不妥,为什么不直接和主席谈?”彭德怀回答:“现在的情况,没人敢在会上发言,我必须提出来引起重视!”黄克诚长叹:“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感情深厚,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谈?” 彭德怀,这位以指挥打硬仗、恶仗、苦仗而声名显赫的军事巨擘,其传奇并非仅仅局限于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尽管他常以“丘八”出身自谦,让世人误以为其文化底蕴或许稍显浅薄,理论修为不够深厚,难以拥有系统且深刻的思想体系。然而,当我们轻轻翻开他那沉甸甸的《军事文选》及其他精辟论述,便会惊讶地发现,这样的看法实则大谬不然。 回溯往昔,1929年10月,彭德怀在《红五军军委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向湘委的报告》中,深入且细致地总结了红五军游击战术的核心原则。他强调,在革命形势距离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尚有漫长路程之时,“红军所能依赖的唯一且行之有效的战术,便是竭力避免正面硬碰硬的战斗,打破敌人倚仗险要地形进行顽固死守的僵局。我们应当巧妙地避开敌人的强大之处,而专攻其薄弱环节,以击溃小股敌人为上佳策略”。“总而言之,红军当前的游击战术,必须依据具体的地形条件和敌情变化,灵活地采取集中或分散的作战方式,以最佳策略应对复杂多变的客观环境,切忌僵化地固守某一种固定的战斗模式。”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在雩都悄然集结,随后撤出中央苏区,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这一重大决策,事前甚至连政治局都未曾讨论过,仅有核心的少数几人知晓。当时,人们并未将其明确定义为“长征”,更未料到会走得如此遥远,只是将其视为一次大规模的转移,意图将根据地从江西迁至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 出发前夕,彭德怀突然紧紧握住杨尚昆的手,深情地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了,今天让我请客,留个纪念吧。”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走到雩都城外的一家酒铺,买了两条鱼和一瓶酒。彭德怀一向生活简朴,除了拒绝领取“公家津贴”外,平时也鲜少花钱。此番请客,实属难得。席间,他一边为杨尚昆斟酒,一边感慨道:“前几次反‘围剿’都打得那么顺利,可这次……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力明明比以前强得多,却落得如此下场……”话语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抑郁与愤懑。 彭德怀不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以卓越的指挥才能为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更是在理论探索的道路上,特别是在军事思想的领域里,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他的诸多论著,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广阔天空,成为了党的集体智慧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周恩来是彭德怀最敬佩的人。 中学时代的尾声悄然临近,周恩来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反复思量,最终毅然决然地决定踏上出国留学的征途。他深知,唯有走出国门,方能探寻到拯救民族于危难的真谛。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之道,无不将目光投向西方。周恩来心中虽有一个美国梦,渴望在那片土地上汲取知识的甘露,然而家境的清贫却如一道冰冷的铁门,将他的梦想牢牢封锁。就在这希望即将破灭之际,好友吴达阁如同春日里的一缕暖阳,慷慨解囊,愿意资助他一笔路费,助他踏上前往日本的求学之旅。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周恩来的生活却异常清苦。夜晚加班时,饿了便只能买点烤白薯或烧饼充饥,从未舍得下饭馆。当时虽有电车代步,但他和潘世纶却因经济拮据而舍不得乘坐,每天从家步行到办报的地方,半夜后又步行回家。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更让他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坚持自己的信念。 在主持会议和处理各种问题时,周恩来更是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从不唱独角戏,而是努力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民主氛围,鼓励大家各抒己见,特别是发表不同意见。他深知,“多谋”来自民主,“断”则是集中的体现。即使面对错误的意见,他也从不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倾听,循循善诱,用事实和道理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在讨论重大经济问题时,他更是专门邀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甚至邀请民主党派的同志参与讨论,让大家都能畅所欲言。 他认为,只有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自由与民主,才能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工作。他常常以唐太宗能听魏征的不同意见、做到兼听则明的例子来教育干部,强调一个善于处理与群众关系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要自觉地把自己当做群众一员,尊重群众、依靠群众、爱护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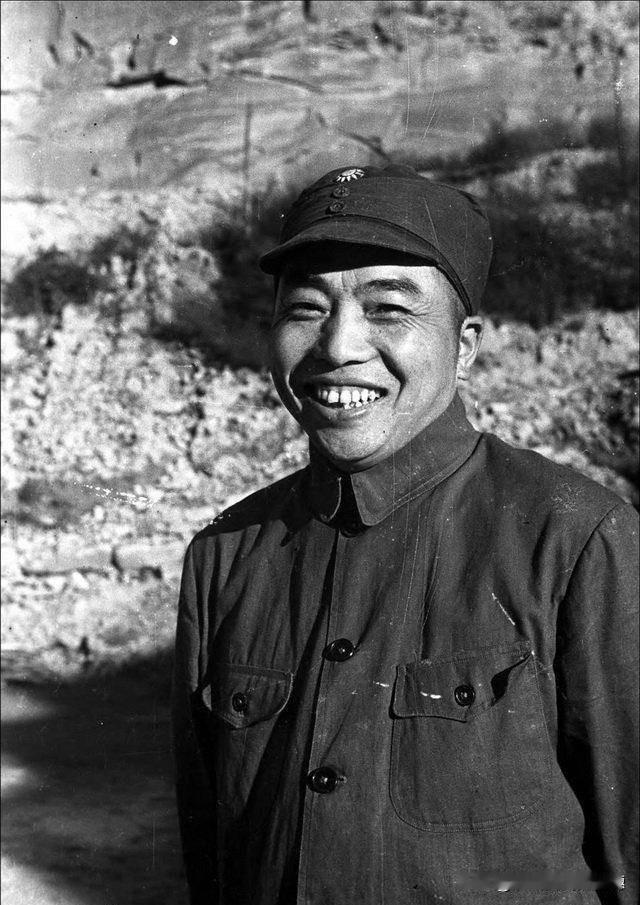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