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那就是历史人物的“两幅面孔”,一是“真实”的形象,一是他“心目中”的形象,前者“写实”,后者“写虚”,前者是史学家的责任,后者是文学家的情怀,《霍去病列传》也秉持这个风格。

司马迁真的对霍去病评价不高吗?似乎是这样,我们看司马公是怎么评价霍去病的。首先,司马迁认为,霍去病出身于低贱之家,却因为是卫子夫的外甥,这叫“幸而贵”,而不是“生而贵”。“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那是一个讲究出身的时代,像李广这种世代豪门的家族是世人仰慕的对象,并且理所当然地占据社会优等资源,这叫“生而贵”。

而卫氏家族仅是个奴隶出身的低贱之家,这种人群被世人看不起,仿佛出身就带有原罪。尤其是卫青、霍去病,他们俩还是都是私生子,活着都是耻辱。他们却因为卫子夫的宠幸而一朝改头换面,这叫“幸而贵”,说白了就是靠裤腰带换取富贵,比小偷还要无耻。“君子豹变,贵贱何常。青本奴虏,忽升戎行。姊配皇极,身尚平阳。宠荣斯僭,取乱彝章。嫖姚继踵,再静边方。”君子豹变,意思是小豹子出生很臭,长大后却脱胎换骨,就像卫家人,陡然从贱到贵,以至于僭越规矩,乱了典章。其次,司马迁认为霍去病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有两大原因,一是装备好,二是运气好。

“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汉匈作战,对汉军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马匹不足,霍去病却因为汉武帝的垂青,拥有最充足、最优良的战马,可以做到一人三匹,丝毫不逊色于匈奴人。另外,老天似乎格外偏心这个年轻人,别人打仗老是迷路,比如李广,老将军这辈子中了邪似的,总是迷路失期。偏偏霍去病动辄奔袭数千里,直达匈奴北庭,却从来不迷路,运气爆棚。最后,司马迁认为霍去病奢靡不仁,待军士很刻薄。“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每次出征,汉武帝都要赏赐霍去病很多酒肉,并且给他配备宫廷厨师,这些食物多到战争结束也吃不完。可气的是,即便这些肉都放坏了、丢掉了、糟蹋了,霍去病也从来不分给部下,以至于士兵们常常饿着肚皮作战,比黄世仁还要坏。以上三点,如果你说司马迁对霍去病评价不高,确实也是如此。不过,这仅是司马迁塑造的霍去病“写虚”的形象,充满了他个人的立场,展现的是文学家的一面,表达的是强烈的爱憎,以及人文精神。当然,这里面也有司马公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与当今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出身论”。如果仅限于此,司马迁就不配被称为史学家,《史记》也不配位列二十四史之首,事实上,除了“文学表达”以外,他老人家还是竭尽笔力,给我们展示了一位罕见的军事天才、一位尽忠报国的热血少年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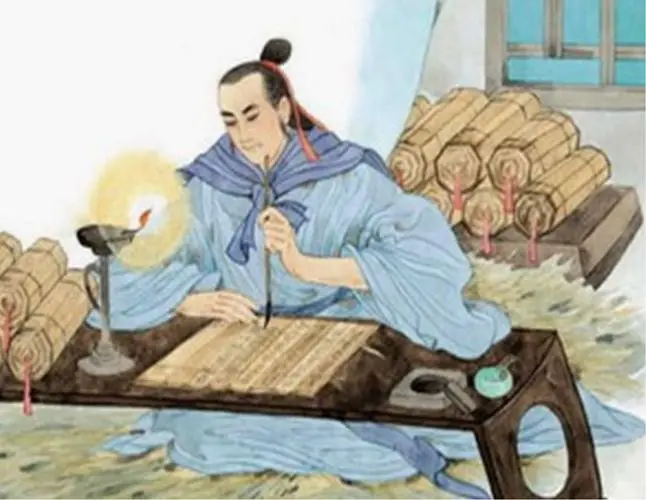
霍去病每一战过后,司马迁总是不遗余力地将他的战功一一呈现,奔袭多远,杀敌多少,俘虏多少,缴获多少,高级俘虏都有谁……言辞中压抑不住大汉帝国扬眉吐气的骄傲,以及对少年英雄的赞美。一句“匈奴未灭无以为家”,成了激励后世华夏儿女的千古名言,并化作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脊梁。“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历史如长河,数千年风流人物,有几个人能得到霍去病那种待遇,留下如此强烈、影响如此深远的标志性痕迹?如果不是司马迁将他对霍去病的敬仰之情融于其中,我们如何有这份感受?

从这个角度讲,司马迁对霍去病的评价很高,如果他只是想一味贬低霍去病,他就会去掉那些热血喷张的描述,留下一个干巴巴的结果记录,再加上前面的三点,今天还有人会记得历史上有个叫霍去病的人吗?这就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史记》的不朽之光,既不缺写实,又通过文学笔法给人物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