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这几天都在聊我表哥的事。
我叫刘建国,在县城开了家不大不小的五金店,日子过得还算顺当。店里卖点螺丝钉、水管,镊子、锤子之类的家用工具,旁边还有块地方修修电器。店面是租的,一年两万多,不算便宜,但好在县城这两年发展还行,赚的钱比村里强。
表哥刘大志比我大三岁,从小在村里就是出了名的倒霉蛋。说他倒霉,是因为他总有一种本事,明明好事抓在手里,却能给整丢了。
小时候他在全乡数学竞赛拿了第一,镇上中学校长亲自来家访,想让他免费念书。结果表哥初三没读完,骑自行车摔断腿,耽误了半年,后来也就没继续读。我爸常叹气说,那时候能考上高中的村里没几个,表哥那脑子,考大学没问题。
屋后有棵老桑树,不知活了多少年,满是疙瘩的树皮像村里老人的脸。阳光好的日子,我们就坐在树下摆个小方桌,打扑克、嗑瓜子,有时扯些家常琐事。
“表哥脑子是转得快,就是命不好使。”二姨夫蹲在树下修着割草机,边上飘着劣质烟丝的味道。他那烟锅子跟了他二十多年,咬口处都磨得发亮。
倒霉归倒霉,表哥人缘倒是不错。他在周围几个村里开了个小汽修厂,换轮胎、补胎、加机油,简单的活都接。嘴甜,会来事,修完车还能陪你聊两句,问问家里情况。村里人有个小毛病,都愿意找他。
五年前那次,是在腊月二十八。
那天我带儿子回村看望老母亲,刚到家,表哥就急匆匆地来了。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袖口还带着机油的黑痕迹。我记得特清楚,母亲正蒸着年糕,厨房里弥漫着甜糯的香气。
“建国,能借我点钱不?急用。”表哥站在门口,搓着手。我注意到他手上的倒刺,像是被什么东西划破了,结了层薄茧。

“多少?”我问。
“二十万。”
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二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是我两年的纯利润。这么大的数,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母亲端着刚出锅的年糕从里屋走出来,听见这数字,手一抖,差点把盘子摔了。
“你要那么多钱干啥?”母亲问,声音有点颤。
表哥不看我们,只盯着地上一块油渍发黄的水泥地面。“想跟人合伙开个汽修厂,县城那边,规模大点的。有个老师傅带着我,技术这块不用愁。”
我跟母亲对视一眼,看得出她不太相信。村里人都知道,表哥有点好高骛远,之前跟人合伙养过鹅,赔了;开过小卖部,关门了;还跟着传销的人去过外地,让二姨夫骑着摩托车追到邻省才带回来。
“你不会又被人骗了吧?”母亲皱着眉头。
“真不是,这次我考察了好久,师傅那边客源稳定,就是缺资金扩大规模。”表哥抬起头,眼睛里难得地露出坚定。
我当时想拒绝的,二十万可不是小数,而且表哥的”创业史”实在让人提不起信心。但那天我儿子正好发烧刚好,母亲说可能是祖宗保佑,让积点德。再加上表哥说只借一年,年后就有收益,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答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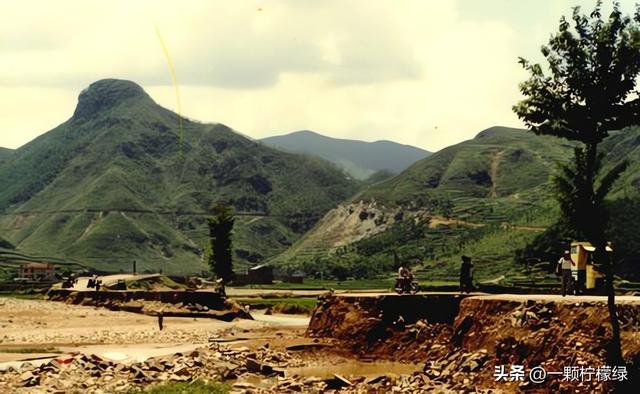
第二天一早,我去银行取了钱,连张借条都没让他写。他拍着胸脯说:“放心,明年腊月之前一定还你,还给你利息。”
钱借出去后,表哥的确开了家规模不小的汽修厂,在县城东边。我去看过一次,地方挺大,有四五个修车位,还真请了个师傅。我心里稍微安心了些。
但好景不长,不到半年,我听村里人说表哥那汽修厂关了。原来那师傅卷了不少钱跑路了,还留下一堆债。
再后来,表哥也不常回村里了,听说去了外地打工。每次过年回来,都是匆匆的,见了我也是低着头,支支吾吾说再给点时间。
母亲倒是宽慰我:“钱财是身外物,表哥不容易,别为难他。”
说实话,我心里早就把那二十万当成打水漂了。五金店日子还过得去,家里也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倒是每次听到老母亲念叨表哥,我心里有点酸。
去年夏天,二姨住院,我去看她。医院走廊墙壁上有块瓷砖掉了,露出里面灰黑的水泥。她躺在病床上,脸色发黄,却一直念叨着表哥的好:“大志这孩子,每月都往家里寄钱,从不间断。”
我有点意外。表哥在外面可能混得还不错?但既然有钱寄家里,为啥不还我的?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我也渐渐不再提那二十万的事。
直到前天下午。

那天天气不好,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我正在店里帮一位老顾客修理漏水的水龙头,手上全是铁锈和污水。店门口停下一辆黑色的轿车,看着挺新的,像是豪车。
我没太在意,以为是哪个客户来买东西。抬头一看,从车上下来的竟然是表哥。
五年没见,他变了不少。身材壮实了,皮肤也黑了,眼睛倒是更有神了,不像以前那么飘忽。他穿着件体面的深色夹克,头发理得整齐,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多了。
“建国,有时间吗?”他朝我招手。
我放下手中的活,走过去。内心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既有久别重逢的高兴,又有关于那二十万的疑问。
“时间快五年了。”表哥笑着说,从口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二十万,加上这些年的利息,一共二十五万六。”
我愣住了,没想到他真的来还钱了。接过信封,沉甸甸的,里面都是现金。数了一下,的确是二十五万六,连利息都算得清清楚楚。
“你这些年在外面干什么呢?”我收好钱,问道。
表哥神秘地笑笑:“去看看我的车?”
我跟着他走到车前。虽然不太懂车,但也知道这辆黑色轿车不便宜,怎么也得二三十万。表哥是在外面发财了?

“打开后备箱看看。”他说。
我按下开关,后备箱缓缓打开。
我愣住了。
后备箱里不是行李,而是整整齐齐码放着的十几本笔记本。最上面那本翻开的页面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汽车修理的步骤、零件编号、常见故障排除方法,旁边还有手绘的零件图解。
“这…这是什么?”我不解地问。
表哥拿起一本翻了翻:“这五年,我去了日本,进了丰田的一家工厂做学徒。”他顿了顿,又拿起另一本,“这些都是我这几年的学习笔记,一共十七本。”
我翻看着那些笔记,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有些地方还贴着照片或图纸,边角都快翻烂了。有些页面上还有咖啡渍,或是油污的痕迹。
“那天借你钱后,我雇的师傅确实卷钱跑了。”表哥靠在车上,点了根烟,“那时我差点崩溃,觉得又一次把事情搞砸了。手上有借你的钱,但汽修厂的设备和房租已经花了不少。”
我默默听着,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复杂而坚定。
“那时候我就想,与其在这继续瞎折腾,不如真的去好好学一门手艺。”他吸了口烟,烟雾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清晰,“有个客户是做日本劳务输出的,说可以带我过去,但要先垫付十万培训费和中介费。”

“你就去了?”
“去了。”表哥笑了笑,“把剩下的钱都用在了这上面。开始真的很苦,语言不通,技术不行,差点被工厂辞退。每天晚上回宿舍,就逼自己学日语,记笔记,研究那些复杂的汽车构造。”
他从后备箱拿出一本最旧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日期——正好是五年前。
“刚开始的三年,我几乎没攒到什么钱,每个月除了寄点回家给爸妈,就只够自己生活。第四年开始,我被提拔为小组长,工资高了一些,这才开始慢慢存钱还你的。”
说着,他指了指车:“这车是二手的,花了八万,前天刚从码头提的,想着正好开回来还你钱。”
雨开始下了,最初只是零星的几滴,打在笔记本的塑料封面上。我们急忙把笔记收回后备箱,关上盖子。
“现在准备干什么?”我问。
“回村里开汽修厂。”表哥坚定地说,“不过这次不是瞎折腾,我有真本事了。”
我看着表哥自信的样子,想起他小时候那个拿第一名的样子,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你那店面还租着吗?”我问。

“早退了,现在想在村口那块地建个简易厂房。”
雨越下越大,我们躲进店里。五金店的灯光有点暗,照在表哥脸上,我才注意到他眼角的皱纹比同龄人多了不少。
“当初我走的时候,全村人都说我又要去瞎折腾。”表哥接过我递给他的茶杯,里面泡着廉价的绿茶,飘着一股塑料味,“说我这辈子就是个废物。”
外面雨声哗啦啦的,打在铁皮屋顶上,像是某种急促的鼓点。
“你知道最难熬的是什么吗?”他问,眼神望向窗外模糊的雨景,“不是工作的辛苦,不是语言不通,而是想到欠着你的钱,却遥遥无期。每次过年回来见到你,我都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店门口的风铃被风吹得叮叮当当响,那是去年夏天一个小姑娘落在店里的,粉色的,上面还画着卡通图案,我一直没扔。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我能理解的。”
表哥苦笑了一下:“说了有什么用?你会更担心钱打水漂了。与其听我解释,不如等我真正有能力了再来见你。”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想起表哥那些年的倒霉事,想起村里人背后的议论,想起他那些失败的尝试。
“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在乎那二十万。”我轻声说。

“但我在乎。”表哥放下茶杯,声音很坚定,“那不只是钱的事,是我对自己的承诺。”
雨声渐小,店里的日光灯闪了两下,发出嗡嗡的声响。
“那十七本笔记,我想送给你儿子。”表哥突然说,“他今年该上初中了吧?”
我点点头:“是该上初中了,成绩还不错。”
“那就好。虽然那些汽修知识他可能用不上,但我希望他能明白,人这辈子,无论多大年纪,只要肯学,总能重新开始。”
雨停了,阳光从云层中透出来,照在柜台上那把生了锈的老剪刀上,反射出一道微弱的光。
第二天一早,表哥就开车回村了。我送他到店门口,看着那辆黑色的轿车渐渐远去,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昨晚回到家,我把表哥的故事讲给儿子听,还给他看了那些笔记。儿子对那些复杂的图纸很感兴趣,缠着我问这问那。
“爸,我以后也能像表叔一样厉害吗?”临睡前,儿子问我。
“当然可以,只要你肯努力。”我摸着他的头说。

今天上午,我接到村里二姨的电话,说表哥回村后,直接去了村委会,申请了那块地。村长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还说要帮他宣传宣传。
“你表哥这次是真的变了。”二姨在电话里说,声音里带着笑意,“他昨晚把这些年的笔记给你爸你妈看了,你妈看完都哭了。”
放下电话,我看着店里那些大大小小的五金工具,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也许,我可以跟表哥合作,把我的五金店和他的汽修厂结合起来。县城到村里也就二十分钟的车程,来回不算远。
窗外,阳光正好,照在店门口那个褪了色的招牌上。多年来第一次,我认真思考着扩大生意的可能性。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你以为丢掉的东西,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你认为是结束的事情,或许只是另一个开始。
就像那二十万,我本以为是打了水漂,没想到它真的帮表哥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而对我来说,得到的不只是钱,还有对生活的一种新的理解。
店门口的风铃又响了起来,是一位常客进来,要买几个螺丝钉。我站起身,笑着迎了上去。
今天的阳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