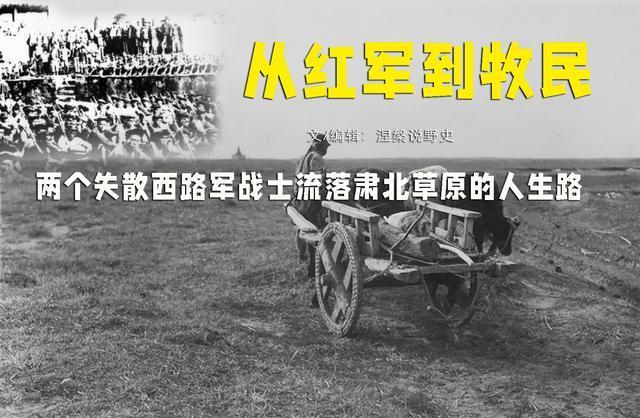
石包城,大家也管它叫壅归镇。汉朝那会儿,它是敦煌郡广至县的地盘。到了魏国,还是沿用汉朝的制度管着它。晋朝时,就归宜安县管了。隋朝呢,又并入了敦煌郡。唐朝时,它归瓜州常乐县管。这个地方啊,一直以来都是保护肃州和整个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卡。有个传说,薛仁贵西征时,曾在石堆上建了个城。谁能想到,1000多年后的1937年春天,一支只剩千多人的红军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里走了43天,又经过了这个地方。
【壹】

何延德,身材魁梧,一头白发掺杂其中,皮肤显得糙而带点黑红。他说话的方式和当地的蒙古族朋友很像,嘴里咕噜咕噜的,卷舌音特别多。大伙儿都亲切地叫他“何娃子”,听说从他小时候起就这么叫了,大家也都叫顺口了。
1933年,何延德才13岁,他就在四川巴中县老家加入了红军。家里兄弟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连鞋子都没穿就跟着红军走了,在三十军的八十九师二六八团里干起了勤务员的活儿。

1937年,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碰到了大麻烦,被西北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他们的部队追得到处跑,还拼命拦截。子弹打光了,粮食也吃没了,周围一个帮忙的都没有。最后,因为人数太少打不过,红军西路军只好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
3月14号那天,西工委的人急匆匆地在石窝山开了个会。会上,大家商量着把剩下的队伍拆成三支小队,然后各自散开打游击。程世才和李先念带着30军剩下的一千多号人,组成了左边的小队,打算往西边去游击。
王树声和朱良才带着5军和9军的剩余部队,再加上100多名骑兵,总共大约700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右支队的队伍,一路往东边打游击战。
高台战斗结束后,新整编的骑兵部队,算上伤员、妇女和小孩,大概有一千人左右,他们组成了中支队,在当地开展游击战。

结果,右边那支队伍刚上路不久,就被马家军给盯上了。两边打了一天一夜,右边那支队伍差不多全打光了,从此就消失了。
随后,中支队也碰到了敌人,就在那一晚,又发生了整队覆没的悲剧。
从那以后,就只剩下左支队这一小股队伍,踏进了被大雪覆盖的祁连山。
这时候,左支队心里头没底儿,程世才和几个头头脑脑开了个小会,琢磨着往西边打游击去。可往西边哪个地界儿打,谁心里也没个准谱儿。就像程世才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写的那样:“咱这队伍啊,就像黑夜里的大海上的船,就知道得往前划拉,可到底要划到哪儿去,心里头是真没数。”
可到了第二天,事情有了意外的进展。左支队那唯一的一台电台,在沉寂多日后,竟然奇迹般地跟党中央通上了话。党中央那边给传来了话,“大家得拧成一股绳,保存好实力。”还问了左支队要不要去新疆,说中央打算派陈云和滕代远两人去迎接他们。
经过一番商量,大家伙儿统一了意见,决定前往新疆,并且立马给中央回了电报。

那时候,部队里伤员挺多的,何娃子就被安排去照顾机枪连里一个叫余连长的家伙。余连长是在梨园口那儿脑袋受了伤。何娃子就搀着他,跟着大队人马后头慢慢走。到了晚上,他们就找个之前部队生过火的地方凑合一宿。
第二天下午,余连长倒在了雪地里,一动不动了,只留下何娃子一个孤零零的16岁少年。
傍晚时分,碰到两个生病的伙伴,我们三个人就一块走了。到了夜里,因为没有柴火取暖,我们三个只能挤一块儿,但还是冷得睡不着。等到天边刚有点泛白,能瞅见路了,就赶紧继续赶路。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陶赖河那边,结果又碰到了七个掉队的红军战士。这里面有两个受了伤的,一个是副营长,叫廖永和,还有一个姓洪的指导员和一个班长。他们手上有三杆长枪,十二发子弹,外加两颗手榴弹。于是,我们就又一块儿上路,继续去追大部队了。

小路上杂乱无章地印着些脚印,都是之前队伍经过时留下的。这条路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平地上,一直往西走。北边的山是祁连山的主峰,特别高;南边那座就矮了点,再过去就是青海的地盘了。
到了考克塞这个地方,后来我们搞清楚,这里其实是肃北蒙族自治县盐池湾部落,藏在雪山最深处的一个夏天放牧的地方。在一片大约20亩大的广阔草地上,有拿石头堆起来的简易灶台,还有之前队伍留下的牛头、羊头和野兽皮。他们捡了些剩下的骨头烤了吃,然后就在那儿安顿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到了考克塞河流入疏勒河的那个地方。山崖下边有些往里凹的小地方,当地人管它们叫拉排,我们就钻了进去。每个人分了一小瓷碗的青稞吃了,然后就躺下休息了。
第三天,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洪指导员眼尖,瞅见远处有个人影穿着红大衣晃悠。他转头跟副营长廖永和说:“那边好像有个人,我过去瞅瞅情况!”这二十多天,咱们在雪山里头转悠,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大家都盼着能找个人打听打听路呢。廖副营长琢磨了一下,点头应允了。

没想到洪指导员刚拎起枪,往前走了没多远,也就三十来米,突然枪声一响,他就倒下了,再也没能站起来。廖副营长和那位班长见状,立马抄起剩下的两把枪,冲出了掩体,打算反击。可他们刚迈出几步,大概也就十米远,崖顶上枪声大作,班长立刻就栽倒在地。紧接着,两颗子弹从廖永和的胯下穿过,打中了他的左膝盖,他也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贰】

崖上和崖下加起来有二十多个蒙古人一块儿冲了过来,他们抢走了枪、子弹和手雷,还逮了两个身强力壮、能干活的红军战士。一个名叫杨印树,被留在了石包城给蒙古族的头头放羊,听说现在人已经没了;另一个呢,当时就被押送到酒泉,给马步芳的军队交差了。
另外几个人,看他们身子骨弱,就没搭理。要走的时候,其中有个能说汉语的告诉他们:“赶紧走,你们的大队伍都走了两天了。再磨蹭,马家的人就该追上打你们了!”
大伙儿都巴不得赶紧上路,但廖永和一直躺着没醒,谁也没舍得走,都留在那儿照顾他。过了整整8天,他终于睁开了眼,大家伙儿都乐坏了。可他腿伤得太重,根本没法走,周围全是雪和冰,连个抬他的东西都没有。

他望了望周围的人,开口讲道:“你们别在这陪着我了,赶紧去追大部队!”可谁也不想走,大家都说,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非要扶着他一起去寻部队。廖永和拼死也不答应。
他心里明白,大伙儿都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累得快走不动了,要是再带上他,那肯定走不动了。于是,他一咬牙,狠下心来,说道:“你们干脆找块大石头,把我压在下面算了,这样你们也不用再为我操心了。”这话一出,大伙儿都忍不住抱在一起,伤心地大哭起来。
最终,我们得决定让谁留下来照看廖副营长。大伙儿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心里都没个底,不知该让谁留下。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留下,就等于和部队告别了,在这荒无人烟、大雪封山的地方,以后是福是祸,谁都不好说。

何延德自告奋勇地说:“要不我留下来照顾廖营长吧!”大伙儿都知道他年纪最小,以前还干过勤务和通讯的活儿,就都点头答应了。剩下的人,廖副营长安排胡传基带着去追部队,胡传基可是军里的副护士长呢。
走之前,胡传基他们几个跑到山上到处找,给我们弄了些柴火、牲口的骨头还有皮子,另外,还把他们身上剩下的那点不多的青稞留给了我们,说让我们以后用来生火暖和身子和填饱肚子。
离别那一刻,每个人的眼眶都湿润了。
廖副营长把自己身上最后的20块银元拿出来,递给了正在赶路的战友。那时候,红军干部们在突围时都会带上些钱。遇到蒙族土匪袭击时,因为他们看到廖副营长浑身是血,就没仔细搜他的身。
廖副营长和胡传基老家都在一块儿,都是河南商河县人,那儿离安徽挺近的。他跟胡传基交代:“要是以后你能回老家,帮我跟我爸妈说一声,就说我在西口外没了。”这话一说,胡传基哭得更凶了。解放以后,胡传基真回老家了,也把廖副营长十多年前让他带的话带到了。可到了1956年,廖永和给家里写信时,老人一开始根本不信,还琢磨着是不是哪位好心人假装是他儿子来安慰他呢!

大家伙儿最终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何延德瞅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心里头五味杂陈。但为了廖副营长,他无论如何也得咬牙挺下去!廖副营长双腿不能动弹,整天只能躺着,何延德就把骨头敲碎捣成糊,跟皮子掺一块儿煮成汤,一勺一勺地给他喂。他还每天从大衣里扯出棉花,搁脸盆里煮了消毒,好给廖副营长清理伤口。廖副营长的伤口啊,是两个指头粗细、透亮儿的圆窟窿,他就用煮过的棉花塞进去,慢慢给他擦,把脏血给引出来。
时间一天天溜走,石洞周边那些能填肚子的草根、骨头还有零碎的皮子,全都被吃得一干二净。没办法,我们只能往更远的地方去找点吃的,但又怕被人瞅见,不敢跑得太远。现在,在石洞里头过日子,真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快满40天那会儿,廖副营长能挣扎着站起来,一拐一瘸地慢慢挪步了。就在这时,突然闯进来三个骑着马、扛着枪的家伙。他们看上去都挺横,就像是出来打猎的,一进洞就开始乱翻东西,嘴里还嘀咕着蒙古话。

看了一圈没啥能拿的,有个人端起枪想解决掉廖副营长和何娃子,但被另一个人把枪口给拦下了。那个稍微懂点汉语的说:“你俩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别乱窜,过个两三天,自然会有人来给你们送东西。”
【叁】

过了三天后,一位大概四五十岁的蒙古族大妈,带着她家的小男孩,给何延德他们拎来了几斤青稞、几斤面粉,外加一小袋盐。这位蒙古族大妈会讲点儿汉语,她说道:“这点吃的,你们先将就着用!”接着,她又好奇地问起他们是来这儿做什么的。
廖副营长瞧着她心眼儿好,就直截了当地讲:“咱们是共产党的人,红军队伍,专门给苦哈哈们撑腰的好汉。队伍打了败仗,这才流落到这地界儿。”
她应声道:“过几天,我们牵马来背你们,帮我们照看羊群,行不?”廖和何两人都连忙点头答应。

蒙族大娘离开后,何娃子立马动手生火弄吃的。他们好些日子没正经吃过一粒米了,饭还没熟透,那香味就直往鼻子里钻!但生怕粮食不够,不敢敞开了吃,每个人就着两小碗,勉强填了填肚子。
过了三四天,那天跟蒙古族大婶一块来的小伙子牵来了两匹马,把廖和何两人驮走了。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位蒙古族大婶是盐池湾部落首领马希的亲妹子,她老公叫管嘉,是个打猎的好手,脾气也挺冲。他年轻时家里没牛羊,就靠打猎过日子,夏天逮八岔草鹿,冬天猎野牛。那时候,一对八岔鹿角能卖120块银洋,管嘉手气好的时候一年能打10对,差的时候也有三五对。
那时候,野马河那块儿,野牛漫山遍野,比家里养的牛还多。管嘉打到的野牛,皮扒下来,肉吃不完,就直接分给邻里乡亲们。那些吃小马驹和小牛犊的狼,包括雪狗和猞猁,在管嘉眼里都不值一提,打猎时顺手就解决了。

就这样,年轻的管嘉在蒙古族姑娘心里成了大英雄。马希头人的亲妹妹,主动提出要嫁给他。按照蒙古族的规矩,不考虑家境和地位,只要两个人乐意就行。女方那边还得送上牛羊当嫁妆。
管嘉娶了部落头人的妹妹后,这才分到了两百多头牛羊。但这并不算富裕,要达到真正的富裕,得有一千只羊才行。那时候,羊毛不值钱,一斤羊毛只能换两斤面粉,一只羊也就值两个银元。可反过来,买一块伏茶却要花上四块银元。结婚后,管嘉主要靠打猎来糊口。偶尔也会帮帮他的大舅子,也就是那位头人,做点事情。

何娃子和廖副营长被带到了管嘉的家里,管嘉的媳妇江西力,就是那位蒙古族的大婶,安排他俩住在了帐篷旁边的小屋子里。到了第二天,管嘉就把何娃子交给了当地的头人。何娃子心里挂念着廖副营长,眼泪汪汪地不愿意走。
管嘉是个猎人,力气特别大,就像拎小鸡一样轻松地把人给拽走了。廖副营长心里头也一万个不乐意何走,但他自个儿腿脚不便,只能干巴巴地瞅着,一点辙都没有。
【肆】

从那以后,何延德就开始帮部落的头领马希照看羊群,数量可不少,足有两百多只。但他毕竟年纪轻轻的,以前也从没干过这活儿,实在是照看不过来。好在有那位蒙族的大娘江西力,她跟马希求了情,说何延德还是个孩子。所以,马希对何延德还算不错,没太为难他。
他虽然是个部落的首领,但家里没啥值钱的东西,还得受青海那边王爷的压榨和控制。这王爷的位置是代代相传的。一个王爷手下管着24个部落,部落首领由王爷说了算,他看上谁就给谁一顶圆帽子作为象征,要是看不顺眼了,就把帽子收回来,把人给撤了。
各个部落规模和经济状况各不相同,有的部落有一百多户人家,有的呢,七八十户,还有的只有四五十户。盐池湾部落就是个小部落,人数也就四五十户,相对穷困些。对于何延德是红军这事儿,他告诫所有牧民,千万别让马家军知道,大家也都遵守了他的吩咐。这样一来,何延德也就没啥危险了。

何延德在头人那儿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廖副营长在管嘉那里,情况就不怎么乐观了。
管嘉这人挺狠。他主要靠捕猎过日子,日子一长,对待廖副营长就像对待猎物似的,特别残忍无情。
一位蒙古族大爷说,他们被袭击那会儿,是管嘉带的头开的枪。廖副营长留在了他家里,管嘉心里老是不踏实,一门心思想要除掉他,还跟别人讲:“那家伙不是善茬,不能留后患。”好在江西力拼命拦着,管嘉这才没下得去手。
过了俩月,廖副营长就拿着俩木棍给管嘉帮忙放羊。他身子有伤,看不住那么多羊,偶尔丢个一两只,管嘉就狠狠地揍他一顿,打得他够呛。

冬天一到,祁连山里头冷得要命,温度经常掉到零下二三十度。管嘉丢给廖永和一件破破烂烂的羊皮大衣,让他白天披着挡挡风,晚上盖着暖暖身。每天早晚,就给他半碗炒面填填肚子。白天饿得他直难受,就等着天黑能好受点。可一到夜里,又冷又饿,虱子还一个劲儿地咬,他又开始盼着天赶紧亮。
他身上的虱子多得吓人,皮袄里头密密麻麻,羊皮都快被盖住了。好心的大娘江西力看他可怜,有时会悄悄给他留点吃的,像是剩下的汤水骨头啥的。可这事要是被管嘉撞见了,连带着江西力也得挨一顿骂。
7月份,马步芳在酒泉的一个手下,带了十多个骑马的士兵,跑到草原上找那些走散的红军。这事儿让马希的老伴依布青知道了,她赶紧用马驮着何延德,把他藏到了一个山洞里。她还给何延德留了些粮食和一件毡衣,告诉他千万别乱跑,老实待在山洞里。

那个马家军的副手把马希老伴依布青年轻时领养的汉族小伙子肖娃绑了起来,逼问他:“有没有看到红军躲在哪儿?”肖娃一直摆着脑袋说:“真没见过。”依布青瞧着孩子受罪,赶忙翻出几张兽皮,解释道:“我家可是这一带有头有脸的人家,哪能藏红军呢?这些兽皮,长官您别嫌弃,拿去交差吧!”说完,马家军的副手才带着十几个骑马的人离开了。
回到草原以后,为了感谢头人马希和那些牧民们的救命大恩,何回干起活来特别卖力,还经常主动帮其他人分担。马希看他这么懂事,也越来越欣赏他。因为担心马家军会再来抓他,马希就对外宣称何回是他的儿子。时间一长,何回也慢慢学会了蒙古话,跟马希和那些牧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渐渐地,他也不那么想念原来的部队生活了。
【伍】
1938年寒冬时节,马希领着依布青前往青海去见王爷。结果马希因喝酒过量去世了。过完春节,依布青独自返回,对何延德比之前更加亲近。尽管别人已经当上了头领,但何延德还是一如既往地帮依布青放羊。
1939年那会儿,管嘉带着一家老小,还有廖副营长,一块儿去了青海的柴达木地区,据说是跑到德令哈西北边的灶火山上放羊去了。有那么一回,廖副营长瞅见远处有栋房子,心里头琢磨着那可能是汉民家,就想过去问问看能不能打听到红军的消息。
他瞅见管嘉正忙着绑帐篷没留意,便把手上的东西一放,弯着腰就往那土坯房冲。还没跑几步远,管嘉就骑着马追上来了,一棍子就撂倒了他,接着又是一连串的棍击,直到把他给打得不省人事。

廖副营长心里那股子念头还是没灭,隔了阵子,他又试着逃跑,结果又被逮住了。管嘉训瞅着他,直言不讳地说:“你这位共产党的副营长,给我放了两三年羊,心还惦记着回共产党当官?行吧,我今儿个不取你性命,把你交给马步芳,到时候是福是祸,就看你的造化了!”
他叫手下把廖副营长绑起来,准备送往西宁。可当他们走到巴音河时,押送的人听说西宁那边土匪横行,觉得路上不太平,便转头把廖副营长带回了原地,交给了管嘉处理。

1940年那会儿,有些哈萨克人被盛世才从新疆撵了出来。他们拖家带口,老婆孩子跟着,就是没牛羊没家产,就带点马匹和几头驮帐篷的骆驼,不过男人手里都有枪。一开始,哈萨克的女人们出来找蒙古人讨点吃的,可后来哈萨克男人们就开始抢牲口,甚至动手杀人。蒙古人哪打得过他们,都吓得跑到安西、玉门去了。何某也跟着依布青大娘一块儿逃到了玉门。
1942年那会儿,新疆过来的哈萨克族人跟原本就住在那儿的蒙古人和藏民之间起了冲突。德令哈这地方的蒙古头头和有点家底的牧民,都带着老婆孩子跑了。管嘉他们一家呢,也跟着大伙儿一块儿逃难了。
廖副营长瞅准机会,甩开了管嘉,然后换了个新身份,连名字都改成了黄永和。他在巴音河旁边挖了个地窖安家,靠给人修靴子过活。他本名叫廖永和,但现在大家都喊他“黄师”,就是黄师傅的简称。

那时候,附近有个蒙族姑娘,在给人家做帮手,名叫格民。她本来是属于格尔木那边的西乌图美仁特其尔部落的,但因为逃难,和家人走散了。格民独自一人来到了德令哈这边,后来碰上了廖副营长。
他们俩老在巴音河边聊着各自的倒霉事儿,日子久了,俩人就产生了感情,住在了一块儿,还生了娃。不过,他们还是一直在德令哈和都兰县附近给人打工,居无定所。
【陆】

1949年9月份,德令哈那地方都在传,“解放军把马步芳给赶跑了”。当地的那些反动牧主啊,心里头都有点发憷。廖副营长那会儿也是头一回听到“解放军”这三个字,压根不知道这是哪路神仙的部队。
他心里琢磨着,解放军既然跟马步芳干上了,那八成就是共产党的队伍,这让他心里头乐开了花,琢磨着去西宁瞅瞅情况。
殿伯尔这个当地的坏牧主,得知赶走马步芳的是共产党的队伍后,心里就嘀咕上了。他还晓得廖永和以前当过共产党的营长。殿伯尔生怕廖永和跟共产党串通一气,把他们给引来,就琢磨着趁人不备,用枪偷偷解决掉廖永和。这事儿让尕尕尼尼三兄弟给听到了,他们立马行动起来,把廖永和给藏得严严实实的。

他们都是生活困难的放牧人家,心疼廖永和,遇到事儿都会搭把手。对于那个总欺负大伙儿的反动牧主殿伯尔,他们心里早就不满了。他们直接跟殿伯尔挑明了:“你要是敢动枪打廖永和,我们也不会放过你!”因此,殿伯尔一直没敢轻举妄动。
这时,刚好有个牧主要去塔尔寺拜佛,离西宁不远。廖副营长就跟他搭话:“我也想一起去拜拜,不如我帮你牵骆驼吧?”牧主一听,有个免费劳力帮忙拉骆驼,那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廖副营长心里头乐开了花,想着跟牧主一块儿走,路上安全不用担心,吃饭问题也解决了,还省得他自己在陌生路上瞎转悠。最关键的是,他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快要见到共产党了!

走了整整19天,风餐露宿,我们终于抵达了塔尔寺。塔尔寺坐落在湟中县城外面的山腰上,头人赶忙去拜佛,而廖副营长则悄悄溜进了湟中县城里。那时候,湟中县城已经解放了,县委书记尚志田正在给群众开大会,讲着话。廖副营长就站在会场边上,心里琢磨着想听听到底在说些什么。
他十多年没说过也没听过汉语了,加上各地说话口音不同,听了老半天也没搞懂人家在说啥,就勉强捕捉到“减租减息”这几个词。可这时候他心里还犯嘀咕,不敢确认是不是自己人,因为国民党以前也弄过一套“减租减息”的把戏。会议结束后开始表演节目,大家扭起了秧歌,还举起了带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子,这时候廖副营长才恍然大悟。

1929年那会儿,咱们在大别山干革命,打土豪、分地、跟恶霸斗,靠的就是那镰刀斧头的旗帜。到了1934年3月,四川苍溪县的龙王山上,团政委库成模同志拉我入了党,入党宣誓也是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面。那旗帜,就是咱们的党旗,党回来了,解放军,那可是咱们党的队伍!
廖副营长急匆匆地找到县委书记尚志田,眼里泛着泪光,一五一十地跟尚书记讲了自己的遭遇,希望能在这儿安顿下来。可尚书记一句也没听懂,就给开了张证明,让他去西宁找军管会主任廖汉生。廖汉生主任那边也是一头雾水,听不懂廖副营长说啥,赶紧找了个翻译来。廖副营长就用蒙语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个遍。但因为没有谁能给他作证,再加上他一身蒙族打扮,说的全是蒙语,汉语说得磕磕绊绊,部队觉得这事儿挺复杂,挺特别,最后就没收留他。
廖副营长心中满是失落,离别之际,那份不舍如同枷锁般沉重。他步伐缓慢,每走一步都仿佛有千斤重,不时地转身回望,眼眶中闪烁着泪光。自言自语时,声音中带着几分无奈与牢骚:“我思念着党,渴望着党的认可,可当党真正到来时,却似乎并不接纳我。如此这般,难道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苦难吗?既然你们不需要我,那我只能黯然归去,或许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归宿。”

那是在1949年10月,西宁刚解放没多久,有的地方还没完全摆脱旧时代的束缚。省里头的大领导扎西旺徐和周仁山,他们派人给他捎信,让他去省上的青年干部培训班上课。说起来,那个培训班,后来就变成了青海民族学院。
让廖副营长去参加训练班,这是对同志的关心,同时也是对他的一次严格考验。这些事儿,廖副营长心里都有数。
他并没有抱怨,心里只想着审查能快点结束,好让他回去工作。在那个学习班里,海晏县有个奴隶主在学员里捣乱,到处传谣言说:“马步芳要回来了,你们在这儿学习,他一回来首先就要对付你们这些跟共产党走得近的人。”他说的“跟共产党走得近的人”,就是指那些少数民族的同志。这么一搞,训练班学员们的思想就开始有些不稳定了。
廖副营长跟训练班的头头说了那些事儿,还帮公安把那个带头的给抓了,把谣言给压了下去。廖副营长干活儿积极,立场也站得稳,组织上调查清楚以后,1950年3月,又批准他入了党。廖副营长盼星星盼月亮盼了13年的党员梦,总算是圆了。这些年没白熬,苦也没白吃。
1950年的时候,何延德已经30岁了,他找了个蒙古族姑娘,两人就结了婚。
1952年那会儿,何就开始在地方政府干活了,起初是干些杂七杂八的事务,后来升为了乡长,接着又做了公社主任。岁数大了点后,他还管了好几年的县招待所。为了回报依布青老人的恩情,何一直照顾着她,直到老人安详离世。现在何家有7个孩子,4个已经出来工作了,还有两个正在大学里深造,最小的那个还在县里的中学读书呢。

1964年那会儿,何延德回了趟四川巴中县的老家,他老爹那时候83岁了,身体还算硬朗。但没想到第二年,老爹就因为生病过世了。到了1970年,何延德又回去看了看,结果发现老家那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何延德讲过:“我在肃北蒙古族的地界上已经呆了快半个世纪了。咱们汉族人常说落叶归根,但对我来说不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我回四川老家探过几次亲,家里人老想让我留下,可我实在是不适应了,那边太热,又湿,还吃不上牛羊肉。待不了几天,我就又回肃北了。还是这儿适合我,气候、生活都合得来。再说了,我媳妇和孩子们都在这儿呢,他们都是蒙古族。”
虽然他嘴上不说自己是蒙族人,但因为在蒙古待了好多年,慢慢地,他的生活习惯和方式都跟蒙族人差不多了。
1973年,廖副营长回到了他的老家,那地方原本在河南商县,但现在归安徽金寨县管了。他就住在老红军的休养院里。
【总结】

回溯往昔,我们缅怀那些英勇无畏的西路军战士,在河西走廊上,他们不畏风雪,勇往直前。面对“马家军”的围追堵截,他们在辽阔的野外奋勇战斗,巧妙周旋。河西的大地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他们持刀握剑,饮雪止渴,英勇气概直冲云霄。这一幕幕,书写了红军战斗史上最为惨烈而壮丽的篇章。
西路军战败后,不少战士流落到了河西走廊。那时候,甘青地区的百姓们不顾自身安危,纷纷伸出援手,帮助那些走散的西路军战士。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心疼那些受伤的战士,觉得他们挺可怜的;有的人则是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觉得救人一命功德无量。但更多人出手相助,是因为同情西路军的遭遇,也对国民党马家军阀的统治感到愤怒。
获救的西路军战士中,许多人后来在当地安家落户,加入了藏族、蒙古族、回族、撒拉族、土族等各个民族大家庭。尽管生活环境变了,他们心中的革命火种从未熄灭。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成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