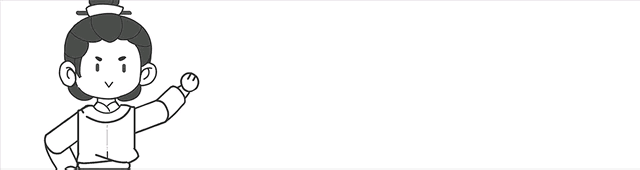
北宋嘉祐二年,也就是1057年,一场科举考试轰动了整个京城,这场考试后来被人称作“千年龙虎榜”。为啥叫这名儿呢?因为参加考试的人里,有苏轼、苏辙、曾巩、张载这些文坛大腕儿,个个都是能在历史上留名的主儿。可您猜怎么着,最后拔得头筹,成了状元的,却是个叫章衡的人。他凭一篇《民监赋》力压群雄,成了千年科举史上头一个“全科状元”。主考官欧阳修看了他的卷子,一个劲儿地感叹:“这卷子格局大得很,有唐宋八大家的风范!”

章衡能赢可不是撞大运。这考试有五场,策论、诗赋、射艺、经史,还有殿试。章衡每场都发挥得相当稳。尤其是殿试的时候,他那一句“运启元圣,天临兆民”,把宋仁宗给打动了。当时呼声挺高的林希,就因为文风太尖锐,落选了。再看苏轼,虽说文采那是没得说,可章衡在策论里展现出来的对民生的关怀,还有治国的方略,更符合仁宗“庆历新政”之后改革的需求。而且章衡他爸章得象当过宰相,家族政绩给他添了不少分,就连苏轼都感叹:“章衡这才能,百年之内没人能比得上。”

章衡的本事可不止在科举上。后来他出使辽国,辽主想刁难他,就拿射箭这事儿来挑衅。章衡也不含糊,连射三箭,全中靶心。这下把辽人给震住了,对他的礼遇直接翻倍。他还偷偷把辽国防务上的漏洞记下来,回国后就提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可惜朝廷没采纳。
在军事实践方面,章衡也有一手。他在河北正定治水的时候,发明了“分洪固堤法”,一年能省7万劳力。在澶州当知府的时候,他废除了禁盐令,主张“疏堵结合”,《宋史》都称他是“盐政破局者”。在财政上,他首创了年度预算制,还揭发了三司吃空饷的事儿,裁掉了3200个多余的官员,给国库省了上百万贯开支。朱熹都说他“理财之法冠绝北宋”。
不过,章衡的改革之路可没那么顺。他为了整顿吏治,顶着压力连着上了十道奏折,还直接跑到中书省跟宰相对着干,把宰相都给逼得认错了。三司使忌惮他的才能,就把他贬出了京城。章衡倒挺乐观,笑着说:“我是为民请命,还怕那些权贵不成?”

除了这些,章衡在文化上也有贡献。他花了20年时间编了本《编年通载》,宋神宗看了直夸“冠冕诸史”。他还修订了《太常因革礼》,重新构建了北宋的祭祀体系,对程朱理学都有影响。
可就算章衡这么有本事,他始终没进入朝廷的核心权力圈。王安石变法那阵儿,他是“改良派”,新党不待见他,旧党也排挤他。
章衡这人啊,慢慢就被人给忘了。为啥呢?一是他文学成就比不上苏轼他们,苏轼的诗词到处流传,可章衡就留下一卷《浦城集》,《全宋诗》里也就收录了他一首诗。二是北宋重文轻武,章衡有武将的一面,像射箭震辽、治水筑堤这些事儿,在士大夫眼里反倒成了短板,他们更喜欢文治。三是南宋文人喜欢苏轼的“士大夫精神”,章衡务实改革那一套和权谋手段,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的“文人政治”。四是章衡这人太低调,“不矜不伐”,不懂得给自己宣传,跟苏轼比起来,在历史上的存在感自然就弱了。
章衡的遭遇,反映出北宋士大夫集团里深层次的矛盾。苏轼代表的是文学理想主义,章衡是务实改革主义,就像“乌台诗案”和“熙宁变法”这两条不同的路。科举制度选出来的是全能人才,可官僚体系喜欢“专才”,章衡这“六边形能力”反倒显不出来。朱熹虽然引用过章衡礼制方面的著作,可更推崇他的理学思想,把章衡“技术官僚”的形象给淡化了。
章衡一辈子践行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誓言,他治水、盐政、财政改革这些事儿,到现在都还有现实意义。这么一个在科举、外交、改革领域都顶尖的“全能型人才”,就因为性格和时代的局限被埋没了。这也提醒咱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光靠“文学想象”,得从更立体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治国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