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汝水清凉 江苏
清明刚过,谷雨在望,赣鄱大地,一派葱茏。自南京抵南昌,再到新余分宜的介桥,去看严嵩故里。严嵩是朱明一代权臣,任内阁首辅二十余载,在《明史》中入《奸臣传》,他也曾在南京任职至少有八年之久。严嵩父子因《鸣凤记》《十三楼》《一捧雪》《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文本,更因《金瓶梅》,被目为大奸臣,遭人厌憎。这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人?且来说说严嵩其人。

早年聪颖,科场顺遂严嵩,字惟中,号介溪。1480年,明宪宗成化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严嵩出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其祖严骥、父严淮,久考未成,悉心栽培、教导严嵩,“惟教此子,他不足计也”,“躬身督课,不辍寒暑,延经师,属生徒,隆礼而饩之,异书厚直购之至,倾其资弗计”。严嵩也曾回忆说,“婉恋为童子,父母不暂离。出门十顾望,恒恐儿寒饥”。严嵩五岁在严氏祠堂启蒙,九岁入县学,先后得县令莫立之、曹忠等赏识,十岁即通过县试,十九岁乡试中举。1505年,二十五岁之时,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严嵩考中进士,为二甲第二名,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其主考官之一,严嵩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与严嵩同科的状元是顾鼎臣,湛若水也与严嵩同年。《明史·严嵩传》载:严嵩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有人出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阁臣李东阳等“咸伟其才”。

1508年,严嵩祖父严骥去世,次年其母撒手人寰,严嵩退官回籍,乡居八载,“一选金马之署,寻返碧山之庐,环堵萧然,吟啸终日”。此时,武宗放浪形骸,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1512年,明武宗正德七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聘请严嵩为总纂。1513年,徐琏继任知府,请严嵩继续纂府志。1514年,正德九年,岁在甲戌,袁州府志成,人称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纠旧志之繁,病续志之略,叙新志来历之详,自有董狐之笔”。任职南京,攀附夏言刘瑾与其党羽被诛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嘉靖年间,明世宗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明世宗宠信,炙手可热。因有同乡之便,严嵩拼命讨好攀附夏言。1522年,正德十六年,年过不惑的严嵩升任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1525年,嘉靖四年,严嵩升任国子监祭酒。1532年,嘉靖十一年,严嵩升南京礼部尚书。1534年,严嵩改南京吏部尚书。南京任职期间,严嵩交游广泛,雨花台、明孝陵、观音山、燕子矶、朝天宫、灵谷寺,多次登临,都有诗作。他有一《观雪登清凉山饯秦司徒》:岩壑风烟积,楼台气色寒。祇园最高处,飞雪更宜看。鹤近瑶空舞,花依綺席漫。中台趣岩召,南斗寄余欢。严嵩还有一《登金陵观音山》江阁凭虚似幻成,绿崖苍壁有人行。波晴日抱黿鼉窟,天险山围脾睨城。万里涛龙争赴海,八埏琛帛尽朝京。谁能数到层轩坐,临水看云失宦情。严嵩曾作《金陵城西泛舟太宰刘公邀集》:叠嶂澄江绕帝州,金樽锦席在兰舟。正逢吏散轩裳集,况是郊晴雾雨收。隔岸帆樯迷浦淑,傍城楼阁带林丘。名都胜概还今赏,赤壁高阳空昔游。王世贞说“嵩诗少年如碧荇依依,水清石见,春云缀空,浓淡有情”。何良骏说严嵩的诗,“秀丽精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胡应麟称严嵩七律是“弘正之后、嘉隆之前第一人”。1536年,嘉靖十五年,年近花甲的严嵩北上赴京朝觐,接受考察,被明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因明世宗对议礼格外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由此与明世宗开始频繁接触。据严嵩自称,当时明世宗忙于同辅臣制定礼乐,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距皇宫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单骑疾驰,快马加鞭。

1538年,嘉靖十七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本欲阻止。明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皇考称宗,岂为过情?”严嵩尽改前说,媚顺明世宗,且“条划礼仪甚备”。兴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仪之争的尾声,严嵩因此而青云直上。反目成仇,诛杀夏、曾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首辅夏言革职赋闲,年过花甲的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终于入阁,成为首辅之一,仍掌礼部事。夏言自视甚高,倚老卖老,对明世宗沉迷道教,不以为然,渐不为皇帝所喜。一日,明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夏言拒绝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佩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明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弃夏言。严嵩又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必欲除夏言而后快,他怂恿明世宗罢黜夏言。夏言最终被罢,严嵩为所欲为,权倾朝野。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之机,继续迫害夏言,“宜将剩勇追穷寇”。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鞑靼入侵河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曾铣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进兵计划。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侍,称夏言“轻启边衅”,严嵩又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夏言、曾铣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信以为真。1545年底,嘉靖二十四年,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明世宗再度起用夏言。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严嵩凭借撰写青词,更加赢得世宗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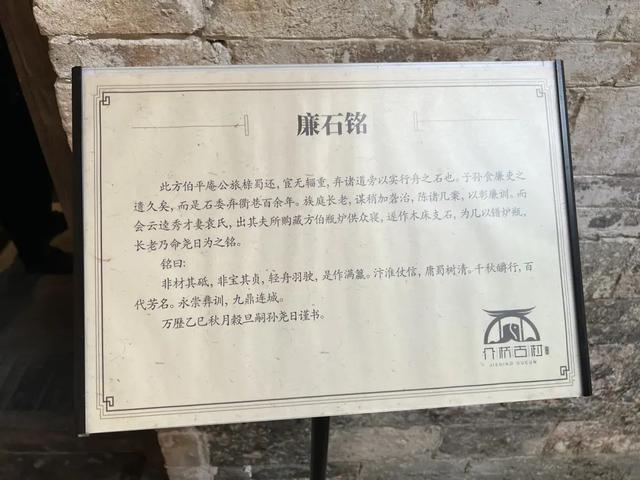
1548年春,嘉靖二十七年,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不可一世。青词宰相,一味迎合明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不老。严嵩一心媚上,全力以赴,不惜人力、财力、物力,无所不用其极。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有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岁费二三百万。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当时朱明王朝太仓岁入不过二百万两,而营建斋宫秘殿的岁费竟至二三百万。斋醮祷祀,需要撰写青词。严嵩因擅写青词而得宠。为撰写青词,严嵩倾注巨大精力,几乎废寝忘食,甚至在庚戌之变时,俺答兵围北京,在城郊大肆杀掠,严嵩竟不顾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仍旧专心致志,大写青词。当左谕德赵贞吉提出抗敌之策,在奉敕谕军之前谒见严嵩,严嵩竟以撰写青词为由坚辞不见。人们因此嘲讽严嵩是“青词宰相”。铲除沈、杨,气焰熏天夏言死后,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之子严世藩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得宠,但并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之事,引起世宗重视警觉。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年逾七旬的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严嵩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印信,使他忧惧而死。嘉靖帝与严嵩之间的芥蒂得以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严嵩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之心,为保住权位,对所有弹劾他的人都施以残酷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炼、杨继盛之死,最为突出。沈炼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严嵩反击,说沈炼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微处分,以避免更大追究,博取清名。世宗谪发沈炼至口外保安。沈炼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严嵩闻之大恨。严嵩之子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炼之名,经兵部题覆,沈炼被杀。杨继盛上疏论说严嵩十罪、五奸,指证他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杨继盛还把世宗最为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相提并论。杨继盛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挂联。但杨继盛在奏疏结尾处却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朱明惯例,藩王不当过问政事,杨继盛提到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杨继盛遂被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此轻而易举诛杀杨继盛。叫板嘉靖,祸民殃国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明世宗仍未确立太子,却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明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这虽是以前亲王旧例,严嵩则提出疑问,“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提出,“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追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徐学谟后来评论严嵩此举,“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严嵩又咄咄逼人地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

光禄寺库银,嘉靖十五年前积银八十万,自二十一年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面对日渐恶化的政局,严嵩不仅没有提出任何规谏和改革方案,且推波助澜,局势更乱更糟。严嵩认为,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应受任何制约;臣下对皇帝只能顺水推舟,唯命是从,以讨得皇帝恩宠。凡是明世宗喜欢听的,即使是很不该说他也说;凡是明世宗想要做的,即使是荒唐可笑,他也毫不犹豫地去做。此外,他还不时采木、采香和采珠玉珍宝,中饱私囊。严嵩成为内阁首辅之后,世宗赐他“忠勤敏达”。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藩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尽在掌握之中。朝内大臣称严嵩父子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人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屡加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因严嵩把持,“政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就可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当上了临清知州。南京御史王宗茂上疏弹劾严嵩“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往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胜计,金银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于府地之后积石为大坎,实以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计。”刑部主事张翀上疏说:“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边卒冻馁,不保朝夕。”武官中则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结局凄凉,寄食墓庐1561年,嘉靖四十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其亲戚欧阳必进接替。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称,“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勉强答应。严嵩密启内容传出,朝野震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不足道也”。不久,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严嵩夫人去世之后,以丁忧之名,严世藩不得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年逾八旬的严嵩刚好路过。世宗问蓝道行:今天下何以不治?蓝答: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世宗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蓝答:留待皇帝自殛。世宗听罢,久久沉吟不语。严氏父子就此被蓝道行所推倒。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被判斩首,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片瓦不存。《明史》载:时坐严氏党被论者……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严嵩家产尽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1567年,隆庆元年,严嵩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87岁。他死之前,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无人吊唁,曾有绝句: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

二十余年内阁首辅一代权臣,就此谢幕。 严嵩珍爱古人墨宝字画。他闻听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收藏在员外郎王振斋手中,便派蓟门总督王忏前去求购。王振斋惧怕严嵩权势,又不舍得交出这一名画,便找名家临摹一幅送给严嵩。严嵩不知是假,公开炫耀,被曾经装裱过此画的装裱师看破。严嵩怒不可遏,以 “欺相”之罪缉拿王振斋。王振斋供称张择端真迹在其舅舅陆治手中,严嵩终于从陆治手中获得此真迹,王振斋最后死在狱中。因王忏知悉内情,严嵩于嘉靖三十八年即1559年以“治军失机”罪名将他杀掉灭口。李玉根据这一史实编写传奇《一捧雪》,被搬上戏剧舞台。严嵩逐渐失宠势倒,其子被处斩,宅邸被查抄,《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入皇宫。正德年间,田汝耔提学江西,严嵩正困卧钤山,田汝籽不以其位卑困顿,亲自造访敝庐,相与评骘风雅。严嵩将钤山所作诗稿精心抄录相赠,田汝耔视为传家之宝,珍藏四十年后,临终之前转交给其弟收藏,田汝耔弟弟将这些手稿携至京师送严嵩一阅。严嵩复睹旧迹,恍若隔世,作《题田深甫所藏钤山手稿》并旧稿归之,成为书坛佳话。留传至今的严嵩书法作品,可分为榜书、碑文、印文、卷轴四类。前门外粮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门贡院的“至公堂”等,都是严嵩手迹。传,乾隆帝想把“至公堂”换掉,但置换他的御笔和其他人所书,似都不如严嵩,只好仍让严嵩所题高高悬挂。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山东曲阜的“圣府”等也出自严嵩之手。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多说是萧显所书,也有人说是严嵩墨宝。现存于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墓旁的“满江红”词,也都是严嵩作品。严嵩曾于嘉靖三十五年有“题手书千文后”:“予昔养疴钤山,得古法书,山林日永,饱时无事,时有临池之兴,虽风雨寒暑不辍,欧阳公谓学书为静中至乐,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于笥底得旧所临千文帖,率皆断简残楮无足观者,儿辈稍联属以成斯卷,因识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题。”与严嵩有杀父之仇的王世贞评说严嵩,“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湘潭人易宗夔说,“严嵩、魏忠贤相继而起,流毒善类,卒以亡国。”史学家、《明末纪事本末》作者谷应泰评价严嵩,“嵩下有杀人之子,上事好杀之君,身之频死,固亦危矣。又从而固宠持位,鼓余沫于焦釜,餂残膏于凶锋。二十七年杀曾铣,是年杀夏言。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三十六年杀沈炼。三十七年杀王忬。假令嵩早以贿败,角巾里门,士林不齿已矣。乃至朝露之势,危于商鞅;燎原之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误帝,帝实误嵩。欧阳氏劝忆钤山堂,邹御史梦射培垒楼。霍山将诛,第门自坏;申生诉帝,被发见形。嵩父子至此,宁有死所乎!”谷应泰所说王忬,就是王世贞的父亲。

张廷玉说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纪晓岚则注意到严嵩的诗歌,“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 严嵩有《钤山堂集》《钤山诗选》《直庐稿》《直庐稿续》《南还稿》《留院逸稿》《南宫奏议》《历官表奏》《嘉靖奏对录》等,共计200多万字,其中诗作有1300多首。今有人著《严嵩传》《严嵩评传》,宜春学院鄢文龙有《严嵩诗集笺注》。
汝水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