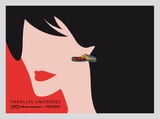文丨冒泡
横店是由徐文荣打造的一个影视帝国,被称作“东方好莱坞”。
这里全年不停运转,见证无数电影和电视剧的辉煌,像是一个追梦的磁场,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实现关于艺术的梦想。
在这些人的背后,则有一个庞大的群体——20万群演,每天穿着不同的戏服,一次一次地站在镜头后。

他们总盼着有那么一天自己能突围,从一群普通群演变成大红大紫的明星。
群演的日常群演的日子实在不像看上去那么舒服,要拼体力和胆量不说,还得比别人会投机。
凌晨三点,便是无数群演争命的开始,他们在宾馆门口、片场外扎堆儿,抢机会、抢收入,甚至抢别人丢下的盒饭。

女演员化妆得注意分寸,既不能让导演觉得粗俗,又不能显得过于普通;
男演员讲究形象条件,肌肉扎实的争取替身活,脸好看的靠外表吃饭,也都精心捯饬。
挑群演有讲究,剧组会派个目光如刀的群头,三两眼扫过去,谁是新来的菜鸟、谁又是老油条,全瞧出来了。
群头要求按剧组给的标准走,譬如要20男20女,人少时全靠群头拍板,人多了就得群演自荐。

男群演往往拉近关系、递烟套好话,女群演用“大哥”相称,笑得甜得腻,倘若姿色过人,甚至能更好拿到机会。
机遇来了,群演却不敢松劲。登记信息后,还得换戏服、学台词,可拍戏往往拖到主演醒了状态好才能开工。
有时等七八小时,熬到中午才轮到镜头。剧组的盒饭虽能裹腹,可滋味一般。

多数时候群演是泥巴血污满身都是,为了真,连水都不好洗干净。
辛劳一天,工钱竟然差得离谱。
有些一小时十几块,一整天能赚个一百了不起,但遇到工资低的,往往只能蹲一天捞几十,活少的连饭也不挣得饱。

群演里也有高收入的群体,比如好身材能做替身,骑马吊威亚玩武术的,或者被分去演情节任务里的丫鬟奴仆,常是两三百一场。
然而群演之间差距悬殊,不少人干几天就遭现实抽了俩耳光,
奋斗也换不来好运气,干脆摆烂,游手好闲,能混一圈就拍戏,不能就抽烟闲聊打牌。
沈凯便是从餐馆跑来的,为了挣家里的饭钱,同时也为了儿时想走进电影里的执念。
 职业转变
职业转变沈凯刚到横店的时候,带着满腔热情想赚更多钱,给妻子和女儿更好的生活。
他靠着能说会道和吃苦耐劳赢得了一些机会,接了不少士兵、死人角色,甚至还抬过棺材。
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可他却很满意这些工作。

他喜欢把自己出镜的片段保存成照片,发给家里,也总对女儿说自己是在体验生活。
女儿更是拿着这些照片到处炫耀,夸爸爸是“演员”,让沈凯觉得有种说不出的自豪,仿佛再累都值了。

但生活总不给人顺顺当当,好不容易攒的钱花得飞快,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偏偏这个时候,一个导演看中了他,让他出演一个有台词的大臣角色,还能赚一笔不低的工资。

沈凯想着机会终于来了,为这个角色格外用心,
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把剧本翻来覆去地看,甚至能把台词倒背如流。

然而到了开机那天,他却彻底怯场了。
不仅眼神游离,动作僵硬,脑子一片空白,连台词都磕磕巴巴地说不清楚。
导演试了半小时,实在没了耐心,丢下一句“太失望了!”直接换了人。

沈凯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回到出租房大哭了一场,
但想到妻子和女儿还等着他养家,他重新振作起来,总结每次试镜失败的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靠着一步一个脚印的打拼和努力。

在后来凭借出演尔冬升的《我是路人甲》电影,被提名第35届香港金像奖新人奖。

这还只是少数人能有这晋升机会,那些年轻群演,把自己收拾得那叫一个讲究。
女孩们化妆特别下功夫。

粉底涂得薄得不会有假面感,细眉弯弯勾勒得刚好,
眼影打得低调却显精神,嘴上涂的口红色号,不会过于鲜艳夺目但也不显单调无光,整张脸就好像刻意没刻意地在发光。
换上戏服后,有的头戴珠花,杏眼含笑,一身古代宫女的模样,满心都是想象着有朝一日也能当个大女主。

男孩子呢,更是对外形的打磨不放过。头发梳得油光水滑,镜头下的每一缕线条都分外小心。
穿上戏服后,那些高挑挺拔的身材让衣摆一晃就透着股英气劲儿,
偶尔扎起袖子,手臂上的肌肉线隐隐浮现,摆出一副专业又自信的神采,心里明明揣着焦急却表面装得淡定优雅。

他们站在片场的一角,时不时偷瞟导演的动静,眼神里藏着期望,盼着下一次灯光打下时,自己也能被喊上一声“男一号”。
结语影视行业的发展,带动了横店群演们的这一片繁忙生活。
只见一群群追求梦想的人,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布满灰尘的片场,为了那一份工作拼尽全力。

每一个镜头后,都藏着一个不甘平凡的故事。
哪怕成功的机会渺茫,他们脸上的汗水与脚步都不会停下,这不是简单的勤奋,而是一种对生活深深的热爱。

都说眼前的风景不一定让人动心,可那个为了梦想跑得满身泥污的人,却常常能让人心头一震。

群演们用行动证明生命的意义不在结果,而在过程中的每一滴汗水。

或许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不会成为荧幕上的焦点。
但在努力的过程中,他们早已成为属于自己的明星,那份勇气与投入远比名利本身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