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也被不少朋友视为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明朝官绅依祖制享有优免赋税的特权。大明是否真的这么爱护官绅,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在赋税上给予官绅这个群体一定的优待,确实是明朝的制度之一,而且这个祖制还是杀官绅如屠狗的朱元璋定的。

(洪武十年二月诏令)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
《明太祖实录·一一一》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又将优免范围由“见任官员”扩大到退休官员,“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不过从头至尾朱元璋承诺的都只是免“徭役”,田亩租税(私田纳税、官田缴租)不在减免范围内。
这项优待政策执行没多久,明廷就发现了大问题,因为一些徭役是不能免除的。明朝的徭役虽然具体种类繁多,但可分为“里甲役”和“杂役”两大类,里甲役和明朝的社会管理相关。
明朝官衙机构只设置至县一级,县以下每十户编为一甲、每十甲设一里。明廷要求“里长”以及望族、科举功名在身者,日常负责管理十甲居民(包括一些民事纠纷的审理)、代朝廷征收粮税、协助官府抓捕人犯、推行朝廷旨令等。
由上可以看出识文断字并了解如何配合官府运作的退休官员和有功名的士绅(他们也被统称为缙绅)是里甲役的核心,这些缙绅为完成这些管理工作,从自家拿出的物资、人力等被称为“里甲役”。
所以这类徭役一旦被免除,大明的基层会陷入无人管理的乱局。因此朝廷很快就默认只优免杂役,即里甲役之外的其它徭役。

这样还没完,对于退休官员的具体优免待遇,朱元璋不仅没有说清楚,执行也没当回事儿(洪武朝能安稳干到退休的官员也不多)。所以从永乐朝开始明廷就不再优免退休官员,认为之前的案例都是太祖的特恩。
官员们都是要退休的,同时也有不少官员觉得这项制度不公平(越富越占便宜),所以朝堂上下不断有人奏请改革。而各代皇帝和一些中枢大臣也认为“一体全免”,太过便宜地方官绅了,不利于地方汇聚民力。
于是在嘉靖二十四年,明廷就出台了那份让很多朋友误解的《优免则例》。
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 … 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内官内使亦如之。外官各减一半。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杂职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粮一石、人丁一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者、免一半。其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之例。
为什么优免的杂役变成了“粮税”呢?这其实是对明朝杂役的一种误解。明朝的徭役派征不光对人头数,还要对赋税的缴纳额度。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针对徭役征发下过一道圣旨,“各府州县官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嗟矣,有不奉行役民,致贫富不均者罪之”。
朱元璋的意思很清楚,征发徭役不能只搞人头平均,要依据纳粮多寡(即家庭财产)去梯次派征,有钱的要多派,这样才能合理抽取民力。(明末征辽饷时,朝廷如果按朱元璋的设想征,钱就不会那么难搞了)。
举个例子来说明下(免丁好理解,这里就不额外说明了)。
某地官府将疏通维护一段灌溉水渠的差役负担定为年50石(负责此差役的家庭得自掏腰包组织人力),派给了县里年纳米60石的周氏。将看管驿站草料仓库的差役定为年30石,派给了年纳米35石的王氏。
几年后,周家子弟因获皇帝青睐,高升为一品大员。这样根据《优免则例》周家在年纳米不变的情况下,徭役可以减低为年30石的标准派发,代替王氏去看管草料仓库了。所以《优免则例》不是直接免除官员对应的粮赋,只是对应降低他们的杂役负担。

了解徭役派发的这个属性后,再来解释另一个“惊人”的免税证据。
(万历三十八年)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常熟私志·赋役》
这个优免政策不是谣言,但它也不是针对全国发布的。只是应天巡抚徐民式为解决税粮运输问题,在江南试行的一种“均役”改革。
经过“一条鞭法”的改革后,明朝也未完全放弃实物征税,每年仍会从主税区(南直隶)征收大量粮食以满足京畿的消耗。但明廷狠在,粮税需在通州仓库核销。换句话说朝廷不负担粮食北运的损耗和运费,需税农或地方官府派徭役解决。
运输税粮这种徭役属于杂役里的“力役”,江南的缙绅们一是觉得根据优免祖制,没自己的事。二是自持身份排斥和普通农夫一起编户齐民(纯劳力),认为这违背了祖训的“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 … 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
注:明末的土地兼并大多不是缙绅直接抢夺、收购普通农户的田地,而是普通农户为逃徭役而将田地投献于缙绅名下,特别是一些科举士子(家族无历史积累,获取功名后免役额度根本用不完)。由于那些田并不真是这些缙绅的私产,所以他们也很抗拒将运粮杂役算在他们身上。
南直隶的官府只能加大普通农户的徭役或者在征粮时加大税粮耗羡,以完成运粮任务。这就是困扰明廷两百多年的税粮北运问题,因为普通农户也不是年年都有余力去完成运粮的,所以南直隶的税粮常会因运费问题而拖欠。
注:南直隶地区第一次大规模拖欠税粮是从永乐迁都开始,到宣德登基时南直隶钱粮最多的苏州府积欠了800万石(后周忱通过设置中转仓、委托漕运统一运输、减税300万石才勉强解决问题)。
徐民式的办法是不搞那些弯弯绕,按照应税田亩数去平摊运粮的相关徭役。为了安抚对朝廷很具影响力的官绅,徐民式将这项徭役的免役的份额参照《优免则例》提高了差不多十倍。超出的部分要么出钱雇人服役,要么自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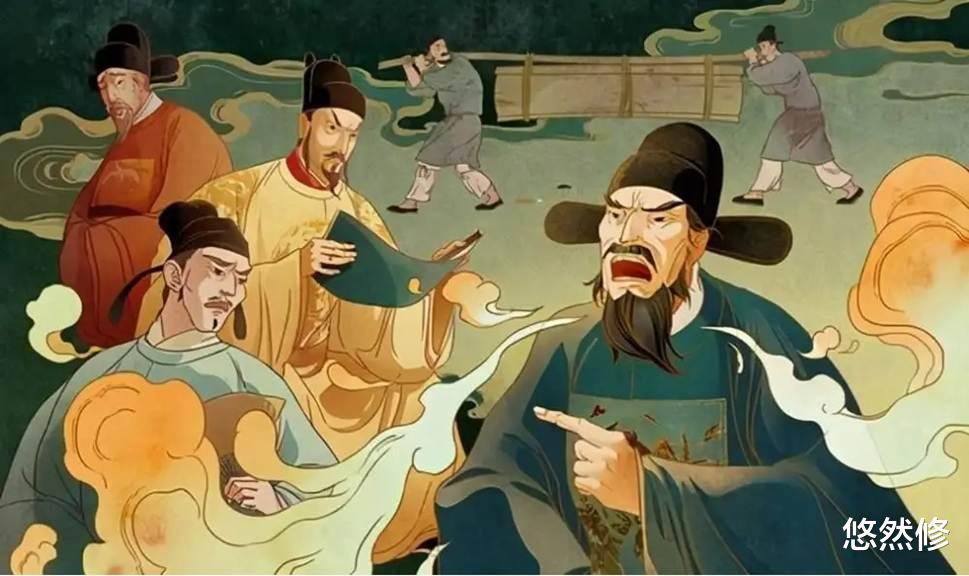
致仕的前首辅申时行知悉后写信怒怼徐民式(申是徐会试的座师),自己马上就要押粮去京师,皇帝如果问我这个老头子为啥回来,我就回答押解粮食向您交差来了。
时任首辅的叶向高倒是很支持徐民式的改革,他替徐民式回复朝廷里的说客,“有田逃役,而无田当差,实不平事。抚臣为地方计,何可深非?且诸公能保子孙他日不为编氓乎”。意思就是已经占便宜就别再斤斤计较了。即便如此,徐民式的改革阻力依然很大,更别说在全国推广执行了。
明朝的官绅当然想拥有不纳税的特权,但综上可以看出明廷从未表露出这方面的意愿。即便是太祖漏口的免徭役,也被明廷和皇帝们削夺不少。毕竟对于皇帝和朝廷,官绅也是被盘剥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