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谥法体系中,“文正”与“文襄”乃大臣薨逝后所能获封的顶级谥号。整个清代,获此二谥的大臣共计23位,细分而言,得“文正”谥号者8人,膺“文襄”谥号者15人(此外,获“文忠”谥号者有10人) 。

在普遍认知里,“文正”这一谥号常被视作极难获取,此观点不乏依据。然而,若从清代对汉族大臣赐予谥号的维度审视,“文襄”实则更具稀缺性。据史料记载,整个清代,获赐“文襄”谥号的汉族大臣仅有三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位获赐“文正”谥号者皆为汉族大臣。
【文正标准很高却未必名副其实】
在清代,谥法体系臻于完备。然而,彼时朝廷对于赐予谥号一事极为审慎严苛。据相关记载,“国朝优恤臣僚,恩礼丰渥,惟身后给谥,最为矜重。”自清朝开国迄至道光一朝,获享赐谥这一殊荣者,仅四百余人而已。
在同治朝以先,针对一品大员,赐谥并非定制。彼时诸多大学士与尚书薨逝后,并未获赐谥号。迨慈禧太后主政之际,遂颁定规制,凡一品官员离世,均赐予谥号。
在古代谥法体系中,获赐谥号本就颇具难度,而欲得“文”字为谥,其难度更是攀升至新高度。依循既定规制,唯有出自翰林者,方具备以“文”字为谥的资格。不过,对于那些虽非翰林出身,却位极大学士之尊的官员而言,也可被赐予“文”字谥号。

在整个清代的历史进程中,于获得以文为谥号的官员群体里,既未取得翰林出身资历,且未曾担任大学士之职者,经考证,仅有索尼与周天爵二人。
在众多以“文”字起首的谥号之中,“文正”“文襄”与“文忠”的等级最为尊崇。
在文正谥号的赐封制度里,存在一项明确规制:凡具备于上书房担任师傅资格之人,依循既定惯例,皆可获赐谥号中含“正”字。
然而,此处所提及的“照例”,实则属于小概率情形。在清代,担任过上书房师傅一职者,保守估计亦有数十人。可见,“上书房师傅”仅构成一项基础条件。但恰恰是这一刚性规定,导致诸如傅恒、阿桂等八旗贵族,皆与“文正”谥号失之交臂。
上书房师傅并非正式职官,而是一种“差遣”,其不具备固定的品级设定。鉴于此,它并不契合“官至一品者予以谥号”这一标准。

换言之,于清朝上书房担任师傅之职者,唯有官至一品大员,方具备获取“文正”谥号的基础条件。然而,即便满足此一条件,也并非笃定能够获此谥号,盖因还存在诸多其他限定要素。具体而言,官员自身的品德操行、才学能力以及所获皇帝恩宠的程度,皆在影响“文正”谥号授予的考量范畴之内。
在清代获封“文正”谥号的八位大臣,即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与孙家鼐之中,曾国藩堪称独特的存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余七位皆曾担任帝王之师,肩负教导帝王学问与治国理政之道的重任,在帝王的成长与教育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而曾国藩并非以帝师身份获此殊荣,他凭借自身在政治、军事及文化等多领域的卓越建树,于清代众多“文正”大臣里独树一帜。
然而,于获“文正”谥号的八位大臣中,曹振镛、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四人,其“文正”之谥,似存“名实难副”之疑。从功绩建树与道德品行等维度考量,此四人与“文正”这一美谥的崇高标准相较,或有不及。相较于陈廷敬、张廷玉等声名远扬的汉族重臣,他们在历史贡献与个人修为等方面,确有一定差距。
从“文正”谥号的赐予情形分析,皇帝的个人情感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依据谥法制度的明确规定,大臣的谥号通常由礼部与内阁负责撰拟。然而,对于“文正”这一谥号,存在特殊之处,即“惟‘文正’二字不敢拟,悉出特旨”,显示出其赐予的特殊性完全取决于皇帝的特别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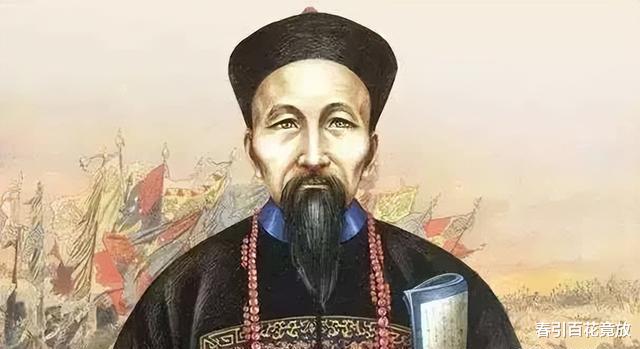
由于帝王个人偏好往往具有局限性,“文正”这一谥号虽居尊崇之位,却未必全然契合受谥者之德行与功绩,其价值亦因之显著降低。
【文襄之谥最隆,少有滥竽充数者】
在清朝时期,共有15位人士获封“文襄”这一荣誉。他们分别是洪承畴,作为明清交替之际的重要人物,其事迹影响深远;靳辅,在水利治理方面颇有建树;李之芳,于政治领域展现出独特才能;图海,凭借军事指挥才能为清朝稳固疆土;华显,以其自身功绩在清史中留下印记;福康安,屡立战功,声名远扬;兆惠,于边疆战事上表现卓越;于敏中,在文化、政务等方面贡献突出;黄廷桂,为地方治理与军事事务尽心竭力;明亮,亦在军事活动中表现出色;舒赫德,在政治与军事领域皆有所作为;勒保,在诸多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长龄,在边疆事务及军事行动中成绩斐然;左宗棠,以收复新疆等重大功绩彪炳史册;张之洞,在晚清的洋务运动等方面影响重大。
于敏中、左宗棠与张之洞三位汉族人士,于历史进程中脱颖而出。需加以说明的是,洪承畴在归降清朝之后,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基于此特定缘由,并未将其纳入此列。
对于对清朝历史具备一定认知的读者而言,以下诸人之名想必耳熟能详。唯“华显”,或存些许陌生之感。华显,身为宗室觉罗,于康熙年间乃声名远扬的封疆大吏,彼时其官声与政绩颇为显著。

在咸丰朝之前,“文襄”这一谥号的赐予尚未形成固定制度。然而,可以明确的是,获赐“文襄”谥号者,需兼具文韬武略之才,且于诸多战事中,立下显著的军事功绩。
洪承畴虽身列“贰臣”之属,然其于清王朝完成中原一统之进程中,所建树之功勋实难以磨灭。顺治十年,洪承畴膺任经略之职,统筹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军事要务,在清廷推行统一策略及实施招抚举措以绥靖各省的进程中,堪称居功至伟。
在清代治水史上,靳辅堪称最为卓越的治河官员。相较于军事征伐,治理河患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与艰难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靳辅凭借长达数十载的不懈努力与全身心投入,成功保障了河运的顺畅。正是得益于他在河务治理上的卓著成效,才为康熙帝顺利平定三藩之乱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撑,同时也确保了江南地区丰富的财赋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财政的稳定与中央政权的运转。
在康熙帝戡定三藩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李之芳与图海功勋卓著,为稳固清廷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而于乾隆时期,福康安、兆惠、黄廷桂、明亮以及舒赫德等人,深度参与了所谓“十大武功”之壮举。他们在各自战事中屡建奇勋,其军事成就皆可著书立传,于乾隆朝军事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勒保与长龄,堪称嘉庆、道光两朝之肱股重臣。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二人运筹帷幄,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智慧;在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进程里,亦凭借其果敢决策与战略布局,立下赫赫战功,为维护彼时国家之稳定与统一,作出不可磨灭之贡献。
上述所列举的八旗贵族,皆历经残酷战火洗礼与生死考验。其于历史进程中,凭借卓越功勋与非凡作为,获“文襄”谥号,此乃名符其实,当之无愧。
对于三位汉臣的情形,需予以差异化考量。于敏中身为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属纯粹文职官员。在大小金川之役期间,他凭借在军务谋划与辅助方面的贡献,立下功绩。故而,其逝后获赐谥号“文襄”。尽管于敏中未亲身涉足战场,但仍因军事方面的功勋而获此谥号。
左宗棠功绩卓著,不容小觑。在晚清时期,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以及回民起义等重大事件。特别是在光绪年间,面对诸多反对声音,左宗棠以坚定决心,力排众议,亲率大军出征,成功收复新疆。其收复新疆这一壮举,意义非凡,影响深远。就这一功绩而言,获封“文襄”之谥号实至名归,即便从更高规格的荣誉衡量,配享太庙亦不为过。

在历史人物的研究范畴中,张之洞的情况独具争议性。张之洞出身于科道系统,这使其与同时期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政治背景与行事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张之洞的声名鹊起,始于其外放担任山西巡抚之后。特别是在洋务运动期间,他积极投身地方实业的兴办,展现出独特的作为与贡献。
张之洞终其一生,虽未投身于诸般战事,但在其辞世之后,经“特旨”恩赐,获谥“文襄”。以张之洞所建之功业而论,纵使“文襄”之谥或存些许过誉之嫌,然相较曹振镛等人获谥“文正”,实乃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退一步言,张之洞至少亦当得“文忠”之谥。
自咸丰朝之后,针对谥号“文襄”的赐予规则出现了新的界定:“文武大臣若于战事中阵亡,或于军营之内因长期操劳而染病身故,且其军事功绩尚未完备者,一概不得选用‘襄’字作为谥号。”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便因“功业未竟”,最终获谥“文忠”。

经严谨对比分析,文襄之谥号所具价值与地位,相较文正并无不及,甚至从获谥之难度衡量,文襄更胜一筹。基于此,御史秉持专业考量,主张在谥号的尊崇序列中,文正与文襄当并列首位,而文忠则位居其次。若各方对这一观点持有相左之见,欢迎于专门的评论区域展开理性探讨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