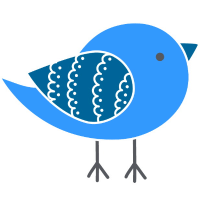1962年夏,父亲带着我们还很年幼的四兄弟回到河南豫东老家,到1974年春末,我们兄弟相继离开,在黄泛区的豫东老家,我们生活了整整十二年。那是一段艰难苦恨的岁月,在那块贫脊的土地上,我们四兄弟艰难地成长着。

回到父亲魂牵梦绕的家乡,父亲和我们经历的苦难几乎是不停不息与日俱增。先是父亲开了不到一个月的小诊所被取缔,接下来是居无定所的无数次搬家和64年遭遇的特大水灾,再就是逃荒要饭,再就是……父亲曾满怀希望和信心申请下放豫东老家的最大目的,是开办一家医疗诊所,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尽点绵薄之力,尽可能解除他们一些病痛之苦。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诊所被取缔啦,安家的钱打了水漂。父亲大半辈子从事的医疗事业,由于自己对政治形势的误判,终于灰飞烟灭。从未下过地干过农活的父亲,便只能从此接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命运,解甲归田的日子并没有陶渊明归田园居的浪漫。
1964年一场仅次于1942年黄河泛滥的水患汹汹而致,大水漫灌,数月不晴。父亲送走两个小弟弟寄居在道湖二舅家里,我们过了两个来月每天领救济粮的日子后,父亲领着四姐和我踏上了逃荒要饭之路。是不是命中注定,我的一生必须要有逃荒要饭的这段历练,否则我难以成长呢。近一年的讫讨生活,差点就让我误以为那或许就是我想做个做稳了奴隶的职业生涯。逃荒回到被父亲苦中作乐戏称的五柳之家,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便真正意识到,“何以为家”就是摆在我们眼前一个最严峻的命题,无须迴避,也回避不了。栖息之处,茅棚草屋遂成了我们最大的心愿。
我们的宅基地是位于村子最西南的一小块空地。宅基地前面就是大队的畜牧兽医站,宅基地后面是牲口马厩。宅基地西南面是一口不大的水潭,这是口季节性水潭,春夏雨水足,水潭的水几乎是满满的,秋天连阴雨时,水潭有一半水,到了冬天水潭则干涸了,宅基地的西面就是生产队的西洼地。逃荒回来,我们在场院住了三天,在头任队长的安排下,队上泥瓦匠高仁义帮忙,我们在宅基地搭了个简易的茅棚。宅基地的茅棚顶还未干透,我们就急匆匆搬了进去。
二弟从三伯家也回了窝棚,他要考初中了,还是位于逊母口镇的太康第八中学。三伯夸二弟,家里一盏煤油灯,几乎是二弟的专属,夜夜挑灯温习功课,考学怕没啥问题。麦收后,我陪同二弟去逊母口参加初中招考,十几天通知下来,二弟也考取了初中。只是二弟入学不久,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一学期书未读完,学校就停课了。停课也好,回来参加生产队劳动吧,我已能挣五个工分,半个劳力了。二弟刚下学,队上只给四分工,他小我两岁,但个头比我高,干活比我行,几个月后也能拿五分工了。这样父亲的工分由六分升到了八分,四姐每天也拿到了六个工分,我们四人顶得上两个整劳力啦。我们天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尽量争取不要再拿钱去生产队买基本口粮。何况母亲一时半会又没找到保姆的活,大姐的工资每月挤出10元钱继续负担两个弟弟,剩余的和母亲节衣缩食勉强度日,再也不可能还有钱替我们向生产队买口粮啦。总之,比之我们刚回豫东的窘迫,苦难的生活明显地好了一些。

67年春天,父亲从长沙把两个弟弟接回了豫东老家,因从二舅舅家转寄到母亲未出三服的本家另一个舅舅家,两个弟弟被虐的生活境况也改变了一些。道湖的寄居生活虽依旧清苦,但毕竟道湖在江南,不像豫东老家的生活粗疏将就,两个弟弟虽仍然清瘦,却也抽了条,长高了些,南方少年的秀丽显然比生活在豫东的我和二弟要帅气许多。一家六口蜗居在秸秆窝棚里,日子照样是艰难的,但都在一起啦,彼此无牵挂,生活是不是又进步了一步呢。三弟小学五年级快念完了,他在道湖完小学习成绩很好,小弟弟读二年级,成绩也很好。父亲还是决定把他们送到张君白小学读书,但三弟死活不肯读书了,一是因家里太困难,二是他觉得张君白小学也读不出个啥名堂。父亲抝不过他,也就只好随他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回过头去想想,父亲一直比较重视读书的,为何那时就随了三弟呢。是迫于家庭困难,是入乡随俗,看老家大多家庭女孩读到初小,男孩读到高小就都回乡务了农呢,还是自己自从开的诊所被取缔,就对读书彻底灰了心呢?兜兜转转读了大半辈子书,最终九九归一还是当上了庄稼汉。但这是父亲自己误判政治趋势而落下的命运结局,会与读书有关联吗。我这辈子一直在解读父亲,父亲生前也和我交淡得最多。无疑我们交谈的中心话题,是对他自1962年绝决地申请下放河南豫东这后半辈子, 命运陡转诀择的对与否。但我们始终就观点相左,看法不一。实在遗憾,我感觉我始终就没能读懂执扭的父亲,如今父亲早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知他可否对自己的后半生有所醒悟或重新认识。
随着我们家除最小的弟弟仍在读书,父亲和四姐及我们三兄弟,我们家算是全员参加到生产队劳动中去了。我们全家投入生产队劳动所挣的工分已够分回我们的口粮了,倒欠生产队的历史结束后,慢慢地我们也开始有了赢余。只是那时工分不值钱,一个整劳力一天挣十分工也就只能抵一角钱左右。低产量高投入,费时费力却没啥收入,那时豫东老家的现状就是如此,日子仍就艰难。
1968年麦收季节一告结束,我们三兄弟每每收工后,仍不歇息,我们就到洼里用架子车拖土堆积起来准备筑基垛墙盖屋。我们先丈量出屋基,又去砖窑购买些碎砖夯在基脚,然后把麦秸秆掺在土里和熟,再用铁钗一钗钗地垛墙。在基脚四围垛一轮掺有秸秆的熟泥,等日晒风吹熟泥垛的墙半干后,就用铁锹铲平。然后又垛上下一轮,一轮轮垛上去,够不着了,就一个站在上面接泥团,一个在下递泥团,三个月后我们兄弟垛的墙竟然有模有样成了一间土房子的雏形。等过了年,开了春,泥墙干透了我们从集市买来横梁,檩子和椽子,以及大马钉,比葫芦画瓢,按图索骥盖好了屋顶。等麦收一结束,我们就把分得的麦秸秆浸上水缮成排盖在钉牢的房椽上,屋顶上。然后再在房顶抹上同样掺有秸杆的烂泥,抹平,一间土房子便在我们三兄弟手中落成了。

我们三兄弟没请一个人帮忙,没耽误一天上工劳动生产,利用下工的间隙,用一年的时间,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终于盖起了一间像模像样的土墙草顶的房子,那份自豪和高兴是实难形容的。关键是从今往后,我们可以在豫东老家安居啦。生产队的人都啧啧称贊我们,艰苦奋斗,自立更生,这三兄弟真是好样的。队上有个半调子挖苦我们是穷发财,高仁义对他喝斥道,你也去试试,看你这熊样,穷也发不了财。穷则思变,的确我们回到豫东老家实在是太穷了。
穷得逃荒要饭,穷得很长一个时期,家中连点灯的计划煤油也购不回,只能摸黑,早早上床睡觉。穷得经常煮面条的盐都要去邻舍家借,有次借盐抓错了,误把明矾当成盐放进锅里,一锅豆子掺红薯干的杂面汤,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穷得买不起柴草,烧不熟一锅面汤,半生不熟也要吃下去,吃个半饱还要下地干活。穷,我们住的秸秆棚,到了冬天五面透风,何来五面,四围加棚顶。夜晚我们一家拥着一床破棉絮,上面遮不住风,下面铺的秸秆穿梭着风,我们一家搂在一起还冻得上牙磕下牙,颤抖不已。春天到了,春雨不歇,夏天到了,夏雨滂沱,秋天到了,秋雨连绵,冬天到了冬雪飘飘。秸秆搭的茅棚往往是外面大雨,棚内中雨,外面中雨,棚内小雨,外面雨停了,棚内还滴滴嗒嗒漏过不停。当雨水漫灌时,常常是鞋飘如船,铺盖透湿。一到雨雪天,父亲便连夜枯坐,怕棚顶垮塌,四围冲垮。这便是我们在豫东老家苦难生活的真切写照,无丝毫夸张。
解决了住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烧锅的柴草。当时豫东老家因一年两季,麦子不够塞牙缝,秋粮便选那些高产的作物来种。除高粱玉米,红薯是首选,但秸秆要喂牲口,红薯叶要晒干留着春荒时吃,红薯藤要喂猪。烧锅的柴草除了秋后的棉棵就只能割青草晒干烧锅用。割草只能是在夏天割青草,而且还只能是中午下工后赶紧去割一小梱草。下午收工太阳一落山就看不见割草了。四姐没回长沙时,总是我领着二弟和三弟一起在中午收工后去割草。后来四姐回长沙去啦,我要做饭,中午顶着太阳下地割草就全靠二弟和三弟俩。割草一般都在玉米高粱地里,而且还要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因为村庄附近的草都被人割走了,而且村子附近红薯地里的草也长得不深。中午太阳正当头顶,炎热难当,一般人都要歇晌午。这时便是我们兄弟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磨快利铲,躬身进入高粱玉米地里,唰唰唰,每割一小搂就钻出来透透风。因为高粱地和玉米地,密不透风,里面太热太热。估计有一梱了我们就要捆绑好,赶紧回家哂在门前平地上,因为吃了饭要洗去一身泥尘沙土,下午还要上工。割草是极辛苦的活,草有时会连根拔起,要将泥土抖掉就会抖一身的泥土,甚至是沙尘还迷了眼睛。只是这种草的火焰还不足,很不经烧。
这样我和三弟便开始去将近三百里外的禹县山区拖烟煤回家烧。第一次是我和本村同学张长德及他们两个邻舍一块去的。我个子小劲不大,一架子车拖六七百斤煤还十分费力。张长德个子高但身材瘦,他能拖一千斤。去时一路我们说说笑笑,吃干馍喝凉水,晚上住三角钱一晚的骡马店,也没觉着辛苦。但拖煤回程,就只能低头拉车,抬头看路,没有气力说笑了。煤拖了回来刚开始不会烧,用柴草点燃,拉动风箱,那煤却不起火焰。有次我急了,半煤半柴草,使劲拉风箱,烈焰冲锅底而且飘出炉膛,别提多带劲。一会一锅红薯就蒸熟了。我喜出望外告诉弟弟们如法炮制,二弟更聪明,他把烟煤稍许洒点水,用厚厚的柴草引燃后,那煤火吐着烈焰在锅底欢快地舞动着蓝紫泛红的火光,把烧锅的人也映得脸膛红光闪闪。于是我们烧锅的难题又解决了,而且冬闲时去拖两次煤就够一年烧锅的燃料啦。
一路拖煤的辛苦是一言难尽的。拖一次煤往返差不多六百里路,除晚上住骡马店,整个白天都要紧赶快跑,一天至少要走十二个小时百把里路。拖一次煤顺利的话六七天,遇雨雪天就要十天半个月不止。从家门口往许昌一百多里,全是平路,但从许昌往西到禹县煤矿却都是弯弯的陡坡山道,路极不好走。上坡要躬身低头,勾着脚趾往上爬坡。下坡更难,身体要扛着车身,别让惯性把你推得太快,握不住车轩就会把你冲下悬崖。我和三弟后来为落户长沙道湖,拖煤卖给砖窑筹钱时,一次就差点冲下悬崖。我由于身板瘦小,挡不住车身,要不是三弟快迅冲到我身旁拖住我的车轩,用身子使劲扛住车身,我早已去见闫王爷去啦。哪里还能在这里描述那段苦难的成长岁月呢。

1970年母亲回豫东看望我们,她看到了她的五个儿女虽过着劳累清苦的日子,但都成长了不少,家里的境况也有所改变,有了自己的宅院和自己筑的土屋,也不再饿肚子啦。女大十八变,四姐巳是快二十岁的大姑娘了,出落得婷婷玉立,漂亮端庄。虽整日下地干活,风吹日晒,但天生丽质,皮肤不但不黑,反而白晰柔嫩,青春靓丽。四个儿子最是母亲日夜的牵挂,除了小儿子在读书,其它三个儿子都成了农民,整日里风里来雨里去,干着超出他们年龄的粗重农活。早晨回到家各自检一筐红薯,拿两个黑黑的杂面锅饼,沾着蒜汁,大口吞咽。中午一回来,一桶凉水洗把手脸,然后一手端一大黑碗黑里泛黄的豆面面条,碗里扔几瓣生大蒜,唏里花啦不到十分钟就倒进了肚子里,擦了擦喷着浓郁大蒜臭味的嘴,舀瓢凉井水嗽嗽口并喝上几口后,遂倒在砖头砌的秸秆床上,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傍晚下工回来,洗了手就从锅底刨出几个用热灰盖着的锅饼,拍打拍打,一口生葱一口馍一口凉井水,便解决了晚饭。夜晚用井水冲洗下脚,在裤脚上擦去水渍便上床拥被而坐,聊几句不咸不谈的夜话,交流下一天干的农活,然后倒头睡去,这日复一日的生活就这么捱着过去。
母亲看在眼中,痛在心里,我的这几个儿子,读书时那么好的成绩,期期优秀,奖状奖品不断,难不成就要在豫东这种地方耗一辈子?难不成注定要成为这里的赤脚农民?难不成他们就不能在学校发挥他们学习的特长和优势做一番能成大器的学问,将来谋个好的职业?唉,我可怜的儿子们呀,母亲看着你们满是稚气却又显现出几分老成的脸面,看着你们除了一个大肚子就是一张皮包着骨的身段,摸着你们满是厚茧的一双终日劳作还未成年的手,你们知道吗?母亲有多么痛苦和自责,你们投错了胎,入错了家门,悔不该当初生下你们。这次回豫东,母亲几乎是夜夜垂泪,哀怨父亲,叹息着我们的未来,思忖着如何改变我们的处境。母亲心里只有一个心愿,但愿我这五个儿女,早日重返南方。
母亲这次回河南豫东住了半个多月,这半个月她整日为我们洗衣浆纱,整日为我们缝补衣裳,整日为我们纳鞋底做鞋帮。她让四姐不要去上工啦,在家帮她为我们兄弟四人每人做了两身粗布裤褂,每人两双鞋。然后母亲领着在豫东老家生活了整整八年的四姐去了长沙。母亲临走交代父亲,好好保护四个儿子,善待他们。母亲回长沙就去道湖找已是道湖大队长的二舅想办法,把我们迁回道湖去。母亲和四姐走后,我们几兄弟都难过了好多天,心里总是空落落的,舍不得母亲和四姐。但我们心底又多了几分期盼,多了些许的安慰。母亲说,想让二舅舅帮忙,争取把我们的户口迁往道湖,那是我们出身并生活了一段时光的地方,那个小小的傍水村落曾留下过我们许多的童年梦想。
母亲和四姐走后的第二年,父亲却因胃穿孔被送进了大新集医院,等待开刀动手术。检查结果被诊断左边胸腔排肋骨已折断两根,肋间神经已被严重损伤已形成软肋骨炎症。胃穿孔好治,开刀缝补穿孔部分,肋膜炎要麻烦些,待胃穿孔治好后,再采取吃药和理疗手法兼治吧。医生痛斥父亲,听说你也是个不错的大夫,为何肋排骨折断了这么久才来诊治呢?父亲苦笑不吱声。在一旁只能抹眼泪的我,也是有苦说不出。
67年春是父亲被批斗最激烈的日子,那时豫东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正闹得甚嚣尘上,而且采取的手段全都是梱绑吊打。造反派基干民兵还大肆夸耀农民运动历来就是天翻地覆的,从不搞温良恭俭让,而是采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手段。父亲几乎难空天日就被大队基干民兵拖去集市上批斗,还美其名曰是去赶集。每次批斗要带着高帽子和纸牌子,还要在脖胫上挂上两头吊有一摞砖头的绳子,勒得脖子青筋直冒。父亲的肋骨就是那时被打断的,具体是什么时候,父亲也搞不清。当时对被批斗的人,还不让卫生院给他们验伤看病,没地方看病,买不到药,得不到及时救治,当然也就只能是忍着拖着。我不知道别处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但豫东老家的批斗却是毫无人性的。后庄有个被打死了的地主,死后说他装赖装死,用门板抬着他斗了好几场,直到尸体腐臭才停止。
麦收后,道湖那边又传来了好消息,说我们原在的道湖那个生产队全体社员已通过我们的落户申请,而且都签了名。只差将签了名的申请报告送到公社审批就可以了,何况二舅舅很得公社李书记的信任,只要李书记同意,这事就妥啦。但前提是还要一笔钱去疏通,这笔钱怎么筹措呢?前面出的那笔钱,二舅说是为了获得道湖村社员的签名同意所需的费用。那是我和三弟已去禹县拖了三趟煤共伍仟多斤卖给砖窑上,换了些钱解决的。这次难不成又要去拖煤吗?我对拖煤都有些心理障碍了,我怕山路陡峭,我怕葬身悬崖。
父亲一拍脑袋,有啦,他对我们说,三伯家的宅子下面是我们爷爷的老屋,四五间全部是砖墙瓦房。但已被黄河大水漫灌时埋在地下至少三丈深的地方,瓦肯定被大水冲碎了,但砖墙冲倒后摞在一起应是好的。何况过去的老砖盖房子好得很,有人会要的,可以挖出来变几个钱。父亲遂去找三伯商量,三伯同意了,前提是挖砖可以,应距离他们现在的房子至少三丈远,而三丈远的地方几乎就是爷爷老屋的边界了,那里能不能挖到砖就看我们的运气了。说干就干,我要做饭并协助母亲照看幼崽们,只有二弟三弟去挖,四弟在上面接砖并负责把挖的砖铲去泥巴摞起来。也真该我们走运,老天开眼了,二弟三弟在三伯划出的范围三丈多深的地底下竟挖出了近五仟口完好无损的大砖。按两分钱一口我们卖了斜钱,交给母亲托转给道湖的舅舅。
1974年,三姐夫的侄儿在湖北监利一个砖厂工作,监利挨着岳阳,那里靠长江边,种水稻很富庶,急需劳动力,根本不要迁移户口啥的,只要是劳动力,去了就能落户,他能够把我们搞定。三姐夫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拍板,要三姐去豫东老家接走我们。尽管当时已到了1974年,天怨人怒的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但豫东老家仍是左派掌权,对像父亲这种政治身份的人及他们的子弟实行着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生产队只能有生产劳动挣工分的权利。像传达林彪叛逃等有关政治敏感的事,我们都是要被基干民兵看起来的。用他们的政治术语是,你们这类人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你们胆敢借机蠢蠢欲动,就要砸烂你们的狗头,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三姐夫是个思维缜密,办事细致的人,他总是把事情的过程预想得十分周密,包括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困难和周折。他知道我们的当时在豫东老家的政治待遇,于是他替三姐写了满满三大张如何带领我们顺利离开豫东老家的计划,如同三个锦囊妙计,藏在三姐贴身的口袋中。三姐也知道这趟回豫东老家接我们去湖北落户的重大意义,她也不敢整过程有任何疏漏,否则此事毁于那一个环节,后果都不堪设想。

三姐到家后遂把父亲和我们三兄弟召集到一起,既介绍了我们将落户的地方是锦绣江南的渔米之乡,又跟我们分析了离开豫东的一些困境和麻烦。并且把三姐夫的三封锦囊妙计展示给我们细细的阅读了数遍。随后父亲又知会了三伯,让三伯也参与护送我们离开老家的种种计划。三伯提出,首先对生产队严密封锁我们离开老家的消息,哪怕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其次在走之前照常上工干活,让别人看不出我们有任何出走的端倪。再就是避开大队基干民兵知道我们出走的消息后,有可能去追捕截获我们的车站和路途,寻一处他们料想不到,抓捕不了的陌生路线离开。还有就是选择在下半夜最夜静人深的时候,轻脚蹑手地走,千万别弄出什么动静。三伯,这个在长沙蛊惑父亲回豫东老家开诊所的始作俑者,他对我们这次离开豫东的周密布署竟是这般滴水不漏,他是追悔反省当年他对父亲家乡概念的误导吗?
今天回想我们离开豫东老家那几天的情形,我仍是心惊胆战,心有余悸,好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让人紧张得心脏随时都要跳出胸膛一般的境地。在今天看来那是一次多么寻常的迁徙呀,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风雨如晦,风声鹤唳,高度政治敏感的年代,即便是寻常百姓的一次再寻常不过迁徙都是多么的不易啊。
1974年的春末夏初之际,某一天的夜半时分,父亲和我及二弟四弟,跟着三姐在三伯的护送下,踏着豫东老家的茫茫夜色,在还有几分寒意的夜风吹拂下,不走庄不串村只选黄泛区广袤平原上纵横交叉的小路,辞别了我们生活十二年,父亲当年绝决申请下放的,他心心念念的老家。那是豫东风沙盐碱地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叫张君白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