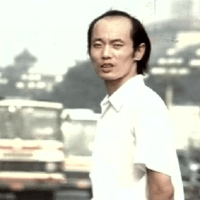我去过最北的地方是中俄边境的黑河,再向北隔江望去,就是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在那儿我裹着军大衣度过了人生中最冷的一个冬天,几个冻得绝望的晚上觉得这里就是人类世界的尽头,没准儿也是我生命的尽头。
人类世界的尽头当然不是黑河,也不是李雪琴的家乡铁岭。后来有几次人到中年的我裹在温暖的被窝里,又萌生了再次向北方进发的雄心,顺手举起手机翻阅了一些人类最北城镇的资料,然后一掀被子就放弃了。
世界上最接近北极点的城市叫做朗伊尔城,坐落于挪威属地斯瓦尔巴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之上。从朗伊尔城再向北去,在斯瓦尔巴群岛北端,还有一座连接人类文明与世界尽头的一座小镇——新奥尔松。
这些名字象征着我未酬的壮志,一直深印在脑海中。

最近的一部纪录片重燃了这个被我封存多年的少年狂想。《光语者》跟随空间物理学博士刘杨踏上了极地征程,中国北极黄河站正位于新奥尔松,镜头围绕这座小镇上的30多位居民,和不远处朗伊尔城中守候极夜、等待日出的人们,为观众还原了世界尽头的人类生活。
影片在开场的几分钟时间里都没有一句对白,只有凛冽寒风的声音、脚步踩过积雪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声音、划燃火柴的声音、木头燃烧的声音、笔尖在纸上书写的声音……在万籁俱寂的、覆盖冰雪的,极夜之中的遥远北方,这些声音组成了一个孤独的梦境。
本以为整部纪录片就要以这样“孤独”的氛围贯穿始终,没想到随着镜头的切换,每一位新奥尔松、朗伊尔城的居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人类向世界尽头追逐自由和梦想的诗篇便多了一行。
朗伊尔城的居民多是矿工后代,祖辈随着轰轰烈烈的欧洲工业化变革来到这里,成为历史的注脚。他们的后代今天成为摄影师、艺术家或者探险家,继续记录祖辈在这片冰雪大陆上开拓的人类印记。
镜头跟着这些居民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摄影师用镜头记录这座矿城的变迁,版画家在画板上定格人与自然的关系,艺术家采集各种声音,用废弃物组成发声和发光的装置艺术,狗场的一对夫妇养了上百条雪橇犬,拉着远道而来的客人了解这座小城。
还有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在这里举办音乐会、组织儿童合唱团、开电音party。突然你会发现预想的孤独并没有出现在影片里,小城居民在漫长的极夜里互相慰藉,仿佛心中有光。

影片以一段极夜的结束为结尾——阳光从雪峰的背面升起,朗伊尔城的音乐家带着孩子们唱起歌谣,这群“光语者”们开心地迎接着“太阳节”的到来;刘博士在这一天离开新奥尔松,小镇上的所有人为他送行;同样需要离开的还有在朗伊尔城生活了50年的探险家,因为这里“不生不死”的法令,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她必须离开这片眷恋的土地。
影片中有一段长达一分多钟的极光镜头,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纪录片画面。影片中的光语者们心中一定也有一束来自人类文明最北方的光芒,才能让他们对自己的一生留下如此的评价。
“如果有机会重来的话,我会把我的生活重过一遍,包括所有犯过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