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平在《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六章中提到,有一种文学史研究以文学经典的“近读”(close reading) 为主要方法,将文学史窄化为文学经典史,以百分之一的文学遮蔽了其馀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

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李玉平认为“远读”(distant reading) 可以代替“近读”,将更全面、注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学史……(页250)。这个distant reading 覌念,源自Franco Moretti 所撰Distant Reading(London: Verso, 2013), 原本的重点是怎样用电脑处理大量文学材料。
有些文学史书写到盛唐时只选高适和岑参二人为边塞诗的核心代表,例如:韩高年的《一本就通中国文学史》(台北联经2011年版) 有“边塞诗人高适、岑参”一章,高、岑以外的边塞诗人,只获提一提名字。

韩高年《一本就通中国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2011年版。
事实上,高、岑之外的其他边塞诗人可能是lesser authors,也就是在名气上不如“巨星”的作者,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lesser authors 的作品较差,只是相对于其他更知名的作者,lesser authors也许产量较少,也许只是未遇知音。下文我们会举出实例。
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有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s一节(p.102),讨论了唐朝七位边塞诗人。本文谈谈这一节的几个要点和相关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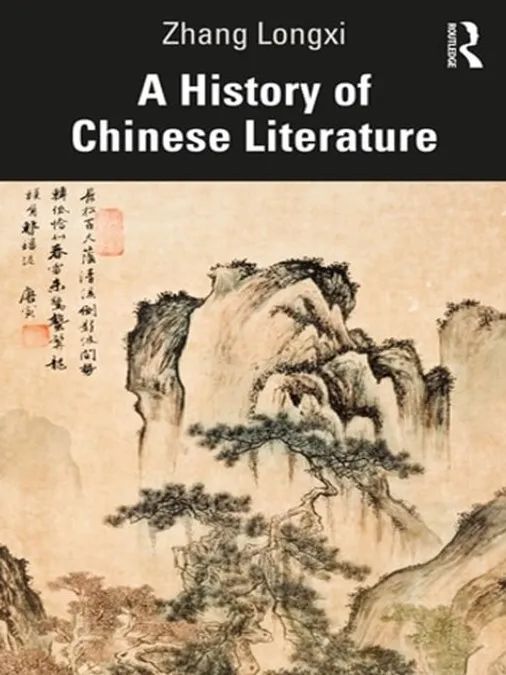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文学上“初、盛、中、晚唐”之中的盛唐,一般指开元(713年12月22日始)至唐代宗永泰年间(765–766),共约53年。台湾学者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讨论过唐诗分期问题后,决定采用这“盛唐53年”之说(《中国文学史新讲》,台湾联经版,页409)。

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
另有学者认为所谓“盛唐”,止于安史之乱,例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中,盛唐是指开元、天宝年间,大概以安史乱起那年即755年为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卷,页253),仅40多年。也有人认为应以杜甫卒年(770年)为界限。
张隆溪教授认为the high Tang period 是roughly from 713 to 755 (p.102)。采用这断限,和袁行霈本文学史的取态没分别(此说的理据似乎是:安史乱起,盛世终结,乱世已临,所以由755年起,就不是“盛唐”了。)
张隆溪教授书中的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所论前四位诗人,生年都在“盛唐”(713 - 755)之前:
王翰 (687–726)王之涣 (688–742)王昌龄 (690–757)李颀 (690–751)王昌龄年纪比高适、岑参都大,然而,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主编本《中国文学史》中,论述高、岑的部分反居于王昌龄之前(游本第三节)。这似乎说明王昌龄的文学地位低于高、岑?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可供参照的是,在山水诗方面,没有出现这种情兄:“王、孟”的排列次序十分稳定。我们没看到“孟、王”之称。王维出生于公元692年,而孟浩然出生于公元689年。孟浩然的年纪比王维大,但是“名次”居王维之后。
张教授大概是按时序(诗人的生年)来安排以上四人在书中出现的次序,而不是按文学成就来排次序,因此,王昌龄居于高、岑之前。
论边塞诗,王昌龄的地位可以比肩高适、岑参。这三人的边塞诗有什么独特之处?中晚唐诗人(如王建、陈陶),作品水平和高、岑、王三人没法比吗?

高适(700—765) 比岑参(约715年—770年) 年纪大十五岁。两人的排名,在近几十年的文学史中有变化(有称为“岑、高”)。这排名可能和史家的评价有关。岑、高的诗篇有何特点?论诗篇数量,谁更多?
高适的边塞诗,早期和晚期颇有差异,尤其是早年的作品出现一些批判性较强的诗篇。

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高适曾在河西节度幕府任职。河西在大唐的西北方,而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97﹔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唐代边塞诗硏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页202) 却写“汉家烟尘在东北”: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全唐诗》卷213)

《全唐诗》
此诗中有“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之句,显然是常见于边塞诗的“内地”“边塞”二元空间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此诗针砭“美人帐下犹歌舞”(在战士大半阵亡的背景下犹歌舞),诗末还直接申诉“沙场征战苦”,毫不违饰从军之苦。我们再看高适的《塞下曲(贺兰作)》:
君不见芳树枝,春花落尽蜂不窥。君不见梁上泥,秋风始高燕不栖。
荡子从军事征战,
蛾眉婵娟守空闺。
独宿自然堪下泪,
况复时闻鸟夜啼。
(《全唐诗》卷2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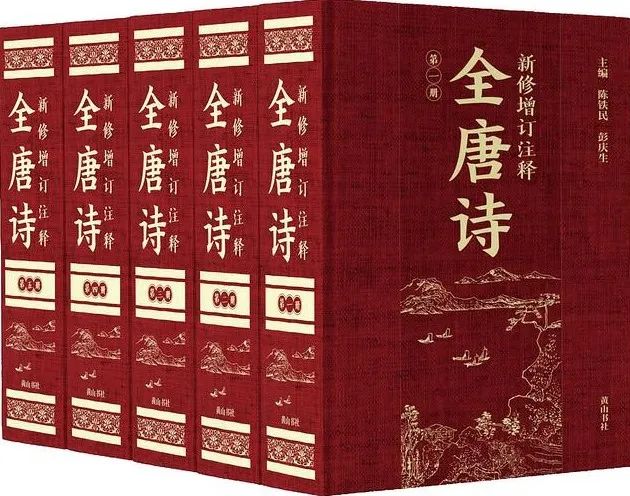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
“荡子从军”句,写军人在边塞;娥眉“守空闺”句,写内地妇人。这又是二元并立,是典型的边塞诗空间布局。
戍边使征人和家人不得相聚,所以边塞诗常写分离之苦,然而,高适却有一首《别董大》,其心态似乎一反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苍凉之感: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全唐诗》卷214 )
虽然高适没说清楚何以天下人人皆识君(董大),但是,我们不妨想象董大将来在边塞建功立业,所以,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大名。
这只是我们的对《别董大》的猜想,不过,猜想有现实依据:唐人从军,确有不少人想凭借立战功而博取朝廷封侯。
高适第三次出塞时期,诗的内容风格转以歌颂哥舒翰的战功为主,不再暴露边塞军营中的腐败黑幕(孙钦善《高适集校注》,页7),有的诗篇甚至歌颂不义之战、歌颂嗜杀。相反,反映士卒受到不公平待遇、个人怀才不遇的诗篇都见不到了(孙钦善《高适集校注》,页8)。

孙钦善《高适集校注》
高适诗今存共约二百四十首,其中涉及边塞题材近六十首。接下来,我们略谈岑参。
岑参边塞诗的成就比高适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因此刘大杰称“岑高”而不称“高岑”,虽然高适的年龄比较大,但是按华人惯例年长者常在排名上常居前,就是排辈分)。
岑参的边塞诗现存六十多首,在盛唐诗人中,作品数量最多,佳作不少。因此,以岑参为边塞诗的代表人物,是很合理的(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台北联经,2011年,页450)。
岑参至少两次从军边塞,先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后在天宝末年任节度使封常清幕府判官。天宝十三年(754年,是安史之乱前一年)岑参跟随封常清赴北庭,任节度判官,历时三年,成了岑参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他写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边塞诗(孙钦善等选注《高适岑参诗选》,页4)。

孙钦善等选注《高适岑参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文学史书几乎必引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为其边塞诗的代表作。 岑参笔下出现火山云、天山雪、热海蒸腾、瀚海奇寒、狂风卷石、黄沙入天等异域风光。此外,他还写了边塞风俗、各民族的友好相处、将士的思乡之情和军营内外的苦乐不均。总之,岑参边塞诗面目多样,不限于杀敌、报国、思乡等“老”话题。
不过,六十多首边塞诗,在岑参诗集中所占比重不大。《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指出:
However,such poems are buta small partof Kao’s and Ts’en’s surviving works, and it does not seem that their contemporary reputations depended on them: none of Ts’en Shen’s poems included in Yin Fan’s anthology are frontier verse……(p.296.Paul W.Kroll 语)。

梅维恒主编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年版。
这句话中的Ts’en Shen就是岑参。岑参现存诗共约403首,可见岑参边塞诗还不足全数的六分之一,所以边塞诗是a small part。
此外,Kroll 注意到: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之中,岑参七首诗入选却未见边塞诗篇(《河岳英灵集》巴蜀书社,2006年, 页202-211)。《河岳英灵集》的成书时间是天宝十二年(753年),这似乎说明:岑参边塞诗在安史之乱前几年还未受到殷璠重视。
近人钱基博评岑参诗:“岑参有王维之秀,而或流华靡。”(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页275)。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
所谓“王维之秀”可能是指岑参笔下景语写得不凡,也可能是指岑参的山水诗有王维之风,实际上,岑参边塞诗就常常呈现边塞的山水 (关于“分流派就是区隔”这一观点,请读者参看2024年3月7日“古代小说网”上的拙文:《王维的归属:文学史家有“立派”“命名”之权?台湾的中国文学史怎样写?》一文)。

“高岑”并称,“高在前、岑在后”也许只是个“历史遗留”。近人刘大杰已经将二人的排名倒过来,成为“岑高”。此外,近人孙钦善、陈铁民等人认为,岑参在艺术上的创造性要比高适突出。
上文提及,较简略的文学史书仅以高、岑为边塞诗的代表。规模较大的文学史书在高、岑之外,会另立一专节讨论其他边塞诗人,例如: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分开两节讨论边塞诗:第三节“王昌龄及其同道”、第六节“高适与岑参”。

《中国文学史新著》
换言之,章骆本《中国文学史》比一般简本文学史多出“王昌龄及其同道”(章骆本 本将王昌龄放在高、岑之前)。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唐朝部分第二章第二节是“王昌龄、崔颢和创造清刚健劲之美的诗人”、第三节是“高适、岑参和创造慷慨奇伟之美的诗人”。
也就是说,袁行霈本和章骆本一样,也在高、岑之前多出一节,由王昌龄领衔。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三个小节讨论唐朝边塞诗:第一节高适;第二节岑参;第三节王昌龄、李颀等诗人。这仍是先高、岑而后王昌龄。
总结以上三本着作的情况:三本都立有王昌龄领衔的专节。
王昌龄近几十年来在文学史书中渐成“唐朝边塞诗第三大家”。其实,王昌龄早就有“诗家天子”之称 (王学泰《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229)。

《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
王昌龄作品也享有盛誉,例如:他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明人李攀龙誉之为唐诗七绝第一。
近年出版的专著中,王昌龄的地位几乎不下于高适,例如:刘冬颖《边塞诗》一书录入王昌龄有十首,比高适入选(六首)还要多。
在张隆溪教授的书中,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这一节涉及几位诗人,征引诗篇,多寡不均:仅王昌龄一人, 就征引了四首(p.104-105)。四首之中,《芙蓉楼送辛渐》不属于边塞诗。另三首是:《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春怨》。
换言之,张教授多引王昌龄诗,略有“近读”(close reading)的意味。

王昌龄边塞诗的特异处:对大唐内部的批评和期望
王昌龄边塞诗有一个特点:他的诗篇对战争有反思,不是一味表达豪迈奋勇不畏死,而是涉及边塞战争的各种“面目”(关于战争的祸害波及身处内地的女人,参看2024年2月23日《古代小说网》上洪涛《唐朝才出现的new genre (新文类)? 新诗篇有没有旧程序?》一文)。

胡问涛、罗琴校注《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
王昌龄《塞下曲四首》之三写“……纷纷几万人,去者全无生。臣愿节官厩,分以赐边城。”这首诗虽然借汉朝事立言,但是,影射唐事之意甚明:唐朝开元年间(十三年)朝廷官厩极度奢糜,简直人命不如马命,王昌龄说要节省官厩之费,分给边城,针对性甚是明确(《王昌龄集编年校注》,页409)。他这种批判锋芒,确实十分尖锐。
王昌龄对于军事带来的灾难,有清楚的认识,他也提出过批判,例如他在《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中说:
独饮灞上亭,寒山青门外。长云骤落日,桑枣寂已晦。古人驱驰者,宿此凡几代。佐邑由东南,岂不知进退。
吾宗秉全璞,楚得璆琳最。
茅山就一征,柏署起三载。
道契非物理,神交无留碍。
知我沧溟心,脱略腐儒辈。
孟冬銮舆出,阳谷羣臣会。
半夜驰道喧,五侯拥轩盖。
是时燕齐客,献术蓬瀛内。
甚悦我皇心,得与王母对。
贱臣欲干谒,稽首期殒碎。
哲弟感我情,问易穷否泰。
良马足尚踠,宝刀光未淬。
昨闻羽书飞,兵气连朔塞。
诸将多失律,庙堂始追悔。
安能召书生?愿得论要害。
戎夷非草木,侵逐使狼狈。
虽有屠城功,亦有降虏辈。
兵粮如山积,恩泽如雨霈。
羸卒不可兴,碛地无足爱。
若用匹夫策,坐令军围溃。
不费黄金资,宁求白璧赉。
明主忧既远,边事亦可大。
荷宠务推诚,离言深慷慨。
霜摇直指草,烛引明光佩。
公论日夕阻,朝廷磋跎会。
孤城海门月,万里流光带。
不应百尺松,空老钟山霭。
(《全唐诗》卷140)

《王昌龄诗集》
王昌龄直接指出“诸将多失律”,令朝廷后悔委以重任。虽然他也强调唐军无惧无畏所向披糜(“有屠城功”),足以迫降戎夷,但是,他又从对手(戎夷)的角度看事情,他说“戎夷非草木”,应该是指:戎夷有智谋,远遁后可以复来,而汉家所占“碛地无足爱”,所以大唐劳而少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王昌龄提到“若用匹夫策”可解外敌之围。
这说明,王昌龄没有忽视“用武力驱逐外敌”,却不是一味歌颂用武力。他寄望“庙堂”能够召集书生论其中的“要害”,也运用他心目的“匹夫策”。王昌龄似乎认识到主战并不能彻底解决边境民族冲突问题。
王昌龄边塞诗篇多佳作,甚得后世的好评,只因数量较少(王昌龄边塞诗共二十多首,相对于高适的五十多首),否则,王昌龄在边塞诗史上的地位未必在高适之下。
下面,我们尝试从“质量”和“深度”方面(而不是“数量”方面)讨论其他边塞诗。

边塞诗中,表现英勇杀敌的诗篇很多,像马戴《出塞词》竟然这样写:“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杨军、戈春源《马戴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112)。

《马戴诗注》
汉人砍杀胡儿(敌人),这样也许让马戴泄了愤、畅了怀,然而,大砍大杀只反映边塞的兵凶战危、作者内心充满仇恨,诗篇本身没有更深层的意蕴(只描写了战况)。
与上引诗篇内容相反,陈陶(约812—885)和王建(约765-830)有些作品内蕴较深,不落俗套,甚有诗史的风范。中、晚唐时期的陈陶《陇西行》其四:
黠虏生擒未有涯,
黑山营阵识龙蛇。
自从贵主和亲后,
一半胡风似汉家。
(《全唐诗》卷745)
此诗开头写汉将擒获“黠虏”无数,这是边塞诗常见的内容,然而,全诗重点在末二句:民族对抗未必需要兵戎相见,自从汉家的公主远嫁胡人和亲之后,胡地习俗已有一半与汉族相似了(参看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中华书局2005年版,页 83)。

《唐代妇女生活与诗》
民族冲突恶化之时,冲突两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十分残酷,不过,有时候民族之间也有交流,例如:李颀《古从军行》结尾:“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页273)。这里“蒲桃”可能就是今天常见的西域物种葡萄。
陈陶《陇西行・其四》写“和亲”,是“黠虏生擒”之外的另一面向。此诗可能是“借汉写唐”:表面上写汉朝公主和亲,暗底里影射唐朝的文成公主(623—680)入西藏,嫁与吐蕃的松赞干布。唐诗边塞诗借汉写唐的例子很多。
边塞诗多写男儿上战场杀敌,妇人居后方思念征人,不少边塞诗都落入这类模式化书写 的框架中 (例如,思妇盼望征夫) ,而陈陶《陇西行・其四》却写内地女子入胡地,改善汉胡双方的关系,促进两邦的文化交流,可谓别开生面。下面,再看中唐诗人王建《凉州行》: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
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
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将绕帐作旌旗。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尹占华《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页1)

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
王建这首《凉州行》首六行写汉家牺牲重大,这与“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意思相同,所以,王建《凉州行》诗首六行已再难有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效果。
第七句以下,奇峰突出,“多来中国收妇女”应该是指:胡人入侵,掠夺汉家妇女为妻。她们生下的孩子多能说汉语(“一半生男为汉语”)。
由于边地长年汉、胡杂处,胡人“如今种禾黍”,也学汉人种庄稼,他们也穿丝织的锦衣,学懂了养蚕织布(第9-14行)。汉人则家家户户学习胡人的乐曲。总之,汉胡对立,但是文化习俗互相影响。
有学者认为,王建《凉州行》写胡人学汉家文化甚多,而汉家死伤惨重却只学了胡乐,这反映王建对大唐国势的忧虑。
实际上,唐朝的胡、汉文化融合是有迹可寻的(龙成松《胡汉同风:唐代民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24年,第九章)。唐人“学胡乐”只是文化交流中的冰山一角。白居易《时世妆》:“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施蛰存《唐诗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489),这说明吐蕃的赭面之风传入唐朝。大唐还从周边羁縻地区引入突厥、契丹、奚族的良马。

施蛰存《唐诗百话》(最新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王建没有在《凉州行》中明确表露褒贬倾向,因此,我们说王建这首《凉州行》表达了民族之间生死相搏之外,有些方面反而是以对方为师。
从诗篇的内文看,王建描写了多年来在边(西凉、蕃)的见闻。他聚焦于外敌的生活(第七行以下),尤其写到“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所反映是胡人世界的生活情景。
王建《凉州行》所写不限于军营和战场上的残杀,反而汉蕃交接的时间“被拉长”(比交战时间长),所写的诸多细节有日常生活的质感,这让我们看到汉、蕃长时间对峙的情况下,人民各自的选择。《凉州行》的内涵超出一般边塞诗甚多。
中唐诗人张籍(约767—约830)在《征妇怨》也描写了征人之妻的生活:“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纪作亮《张籍研究》,黄山书社1986年版,页29),这就是说:丈夫战死之后,女子不仅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依靠,而且也无力抚养尚未出世的腹中之子。

《张籍研究》
不过,文学史书甚少细论张籍的边塞诗。

张教授讨论唐边塞诗,谈到a soldier’sheroic spiritin his audacious defiance of death (p.103)。所谓 heroic spirit, 就是“英雄气概”。在第105页, 张教授又说到theheroic spiritand the sacrifice of soldiers on the frontiers。
这种英雄气概,确是唐朝边塞诗的主调之一。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众多诗篇都是表达heroic spirit,实难出类拔萃。
上文所论王昌龄、陈陶、王建之诗却开拓了新境界。他们的边塞诗中有英雄气概以外的层面,例如:王昌龄的边塞诗提到希望朝廷“召书生”、“论要害”、用“匹夫策”,而不是一味讲英勇、杀敌……
陈陶《陇西行(其四)》、王建《凉州行》都涉及边塞民族的生活和习俗,这两首诗也带给世人一些启示:也许大唐和胡人没有必要世世代代为寇仇、兵戎相见。
“英雄气概”无疑是值得珍视的精神,不过,大唐的边塞诗人并非“千人一面”,因此,“英雄气概”之外,也有王昌龄这类谈及“匹夫策”的人物。 无了期的仇杀、互相消耗,终难化解民族矛盾。民族之间如果尝试互相学习、管控分歧,设法促进跨文化融和,岂非更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唐朝陈陶、王建的边塞诗,内容都超出“勇夫杀敌”的层面,值得重视。

《唐代边塞诗传》

一个lesser author的逆袭:唐代诗僧寒山子
内容大同小异的边塞诗篇(例如表现英雄气概)就算数量很大,其综合价值也未必能胜过一篇有新意、有卓识的短诗,正如半本《红楼梦》的价值足以胜过一大批陈腔滥调的才子佳人小说。
文学史上有些 lesser authors 只是某段时间内的lesser-known authors (知名度较低),若有机缘,他们也可以变成大名家。唐朝的寒山子就是好例子:五四时期,胡适因提倡白话注意到寒山子(胡适将寒山、王梵志、王绩并称为白话诗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寒山诗从日本传译到西方,寒山诗所代表的文化在美国掀起了一阵“寒山热”(与the Beat Movement相关),“寒山热”传到亚洲,触发台湾学术界的寒山研究热潮,详情请参看陈慧剑和叶红珠的著作。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原先次要作者的诗篇(如寒山诗)有某些特质被后人“发掘了”出来而且发扬光大。今人胡安江认为,寒山诗这个案,等同重新“经典化”(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无论如何,寒山诗在日本、在美国,都已经完成经典化(参看《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与寒山诗的经典化》,载陈尚君主编《水流花开: 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 2019年﹔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寒山诗篇在国内的文学史论述中也许仍未挣得“经典”的地位 (如本文开端所说的被“遮蔽”),但是,寒山诗篇却是“国际化”的。
也许有些人会嫌“国际化”语义不清 (难说清涉及多少国),那么,我们改用“跨文化”来描述寒山诗也无不可。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数有国际视野,想必都知道寒山子这个案?
如果成为“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的条件之一是“流通”,那么,寒山诗早已经跨文化流通于域外,尤其是在日本、朝鲜、美国,又有法文、德文、荷兰文的译文专书 (钟玲《中国禅与美国文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92),这史实是无法否认的。民国年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三章第二节已经讨论寒山子……

钟玲《中国禅与美国文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张教授的文学史书 (2023年) 之中,似无寒山子的一席之地。
本文开端引李玉平说“将文学史窄化为文学经典史”,这句话会不会令人联想到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文学史家挑选出来的经典,没有经过个人筛选吗?如果不想将文学史窄化成“文学经典史”,史家可以怎样做?

本文关注高适、岑参、王昌龄在各种文学史书中的地位。除了集中讨论王昌龄外(其文学地位近三十年得到史家的确认),也尝试进行“远读”,发掘高、岑、王三大家之外的边塞诗佳作。限于文章性质和篇幅,本文没有呈现量化分析的结果。
笔者发现,陈陶和王建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两位。其中,陈陶的《陇西行(其四)》内容别开生面。陈陶的《陇西行(其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很受世人重视, 其征引次数超过高适名篇《燕歌行》(参看洪涛《诗史断裂是有意为之? —— 略谈编年体的作用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一)》,载《古代小说网》2024年3月21日)。王建对战场以外的边塞生活有敏锐的观察。
文学史家大多习惯于引领读者“近读”某些经典名作。张教授尤其对“读经典”有心得(参看张隆溪《经典之形成及稳定性》,载《文艺研究》2021年10月;何兆彬《张隆溪:独行于经典之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张教授强调经典有其稳定性。

何兆彬《张隆溪:独行于经典之间》,香港城市大学2023年刊行。
然而,稳定性意味着现有经典必然地位稳固,许多文学史家受制于此“稳定性”“固定性”,谈边塞诗时也就循惯例以高、岑两家的经典名篇为核心,再旁添“三王一崔一李”(王昌龄、王翰、王之涣、崔颢、李颀)的一二佳作而罕及其馀。这样一来,文学史书中的论述也就陈陈相因,出现了大同小异的“文学经典史”。
世人是不是全都满足于既定的“文学经典”?未必。“寒山热”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据说,在欧洲,寒山子的声誉超越李白、杜甫。
当“巨星”被史家 (过滤后留存的“巨星”) 推送到读者的眉睫前,“巨星”就遮挡了读者的视线:读者看不到“巨星”和“经典”之外的史实,这变相造成“遮蔽”。

龙成松《胡汉同风:唐代民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24年版。
在这种“经典有稳定性”的情况下,史书的叙述框架固定,史家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于是,“远读”(distant reading) 只能由我们读者自己来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