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法为诗:江西诗派精品赏析》,钱志熙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4年3月版。

该书为“江西诗派经典选本丛书”之一种,标揭江西诗派的品格之作,对一些文化色彩、文化主题突出的作品进行了集中的论述,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现江西诗派的特点和艺术成就。对江西诗派的诗人诗作在选目上突出大家和名家,兼及小家;在选录作品方面,本书以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为基本依据。在鉴赏批评方法上,一方面尽可能发掘传统诗学中的一些有价值的鉴赏、批评方法,另一方面也尽可能运用现代美学观念和诗歌鉴赏批评方法,期待能做到唯适是用,不以门户、今古为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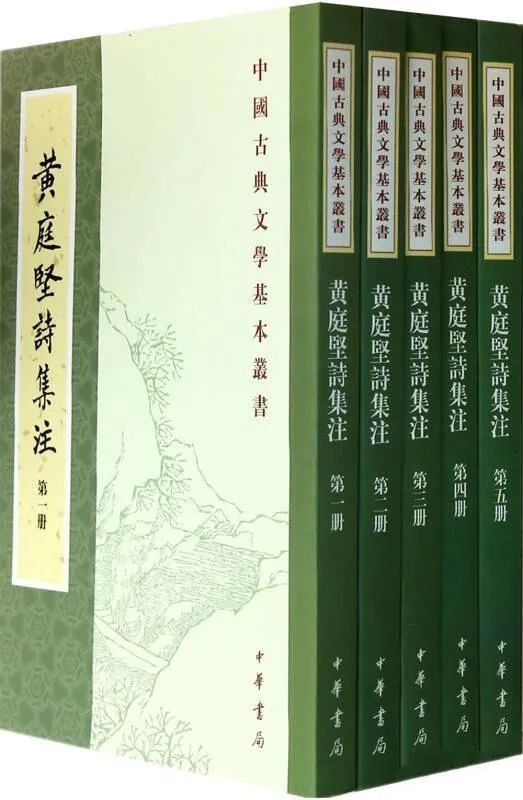
《黄庭坚诗集注》
黄庭坚
徐孺子祠堂
次韵裴仲谋同年
春近四绝句
和答登封王晦之登楼见寄
夏日梦伯兄寄江南
晓起临汝
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
呻吟斋睡起五首呈世弼(选一)
次韵外舅喜王正仲三丈奉诏相南兵,回至襄阳,舍驿马就舟见过三首(选二)
临河道中
汴岸置酒赠黄十七
题落星寺岚漪轩
赣上食莲有感
次元明韵寄子由
上大蒙笼
登快阁
观王主簿家酴醾
过家
送王郎
次韵吴宣义三径怀友
寄黄幾复
以小团龙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
次韵清虚
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
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选三)
双井茶送子瞻
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幹马因论伯时画天马
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
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
题竹石牧牛并引
次韵答曹子方杂言
同元明过洪福寺戏题
六月十七日昼寝
赠陈师道
老杜《浣花溪图》引
题大云仓达观台二首(选一)
竹枝词二首
和答元明黔南赠别
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
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选二)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自巴陵略平江、临湘入通城,无日不雨。至黄龙奉谒清禅师,继而晚晴,邂逅禅客戴道纯款语,作长句呈道纯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
武昌松风阁
次韵文潜
鄂州南楼书事四首(选一)
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

《后山诗注补笺》
陈师道
别三子
寄外舅郭大夫
城南寓居二首(选一)
和豫章公黄梅二首
九日寄秦觏
示三子
雪后黄楼寄负山居士
次韵李节推九日登南山
巨野二首(选一)
除夜对酒赠少章
次韵答秦少章
舟中二首
古墨行
次韵无斁雪后二首(选一)
次韵春怀
河上
和魏衍闻莺
寄泰州曾侍郎
秋怀四首(选二)
绝句四首(选二)
早起
春怀示邻里
和寇十一晚登白门
谢赵生惠芍药三绝句(选一)
家山晚立
寒夜
宿合清口
寒夜
宿齐河
元日
登快哉亭
湖上晚归寄诗友四首(选一)
题明发《高轩过图》
潘大临
吴熙老所藏《风雨图》
江上晚步(四首选三)
谢逸
怀李希声
中秋与二三子赏月,分韵得“中”字
送董元达
闻徐师川自京师归豫章
寄饶葆光
春词(选三)

《倚松老人文集》
饶节
戏汪信民教授
山居二首(选一)
息虑轩诗
岁暮
冬日书谢氏园壁
次韵答吕居仁
山居杂颂(选一)
祖可
书余逢时所作山水(二首选一)
绝句
善权
山中秋夜怀王性之
洪井
洪朋
写韵亭
宿范氏水阁
独步怀元中
洪刍
次山谷韵二首(选一)
道中即事八首(选一)
洪炎
次韵公实雷雨
汪革
寄谢无逸
谢薖
寒食出郊
喜晴
惠洪
西斋昼卧
余自并州还故里,馆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风物类斜川,儿童时戏剧之地也。尝春深独行溪上,因作小诗
晁冲之
复以承晏墨赠之
夷门行赠秦夷仲
李彭
春日怀秦髯
阻风雨封家市
徐俯
次韵可师题于逢辰画山水
春日登眺游宝胜诸寺且观名画
春日游湖上
韩驹
题李伯时画《太乙真人图》
十绝为亚卿作(选二)
代妓送葛亚卿
和李上舍冬日书事
夜泊宁陵
抚州邂逅彦正提刑,道旧感叹,辄书长句奉呈

《吕本中诗集笺注》
吕本中
宿州初暑
春日即事二首(选一)
春晚郊居
海陵病中五首(选一)
次韵尧明见和因及李萧远五诗(选一)
西归舟中怀通泰诸君
丁未二月上旬四首(选二)
赠范信中
夜坐
追记昔年正月十日宣城出城至广教
木芙蓉
柳州开元寺夏雨
高安道中有怀故人李彤
春晚
野岸
兵乱后自嬉杂诗(二十九首选六)
曾幾
题黄嗣深家所蓄惠崇《秋晚画》
汪惇仁教授即官舍作斋,予以“独冷”名之
独青亭
夕雨
雨夜
仲夏细雨
悯雨
岭梅
大藤峡
归途
雪中,陆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
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
挽韩子苍待制
过松江
宜兴邵智卿天远堂
雪后梅花盛开折置灯下
曾宏甫分饷洞庭柑
九日二首(选一)
三衢道中

《陈与义集校笺》
陈与义
题刘路宣义风月堂
次韵周教授秋怀
题牧牛图
风雨
北风
襄邑道中
秋雨
题许道宁画
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选二)
十月
次韵乐文卿北园
钱东之教授惠泽州吕道人砚为赋长句
道中寒食二首(选一)
中牟道中二首
清明二绝(选一)
春日二首(选一)
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得 “静”字
雨晴
送王周士赴发运司属官
试院春晴
试院书怀
对酒
雨
邓州西轩书事十首(选二)
登岳阳楼二首(选一)
巴丘书事
晚步湖边
居夷行
除夜二首(选一)
咏水仙花五韵
陪粹翁举酒于君子亭,亭下海棠方开
春寒
城上晚思
次韵尹潜感怀
立春日雨
伤春
雨中再赋海山楼
渡江
夙兴
怀天经、智老因访之
牡丹


江西诗派的存在,是由南北宋之际的诗人吕本中第一次指出的。他作了一个《江西诗社宗派图》(以下简称“《宗派图》”),以黄庭坚为该派宗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等二十五人,认为他们虽“体制或异”,但“所传者一”,源流都出于黄庭坚(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清乾隆知不足斋刊本《江西诗派宗派图录》
尽管吕氏为突出“江西宗派”这一概念而过分强调了传承关系,相当程度地忽略了这些诗人在艺术上的其他渊源和他们中有些人的独创性,并因此而招致异议。但是,他认为存在江西诗派这一基本看法,还是很快被时人所接受。 如与吕氏同时的另一南北宋之际重要诗人曾幾,作诗赠人云“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另一首诗提到陈师道时也说“豫章乃其师,工部以为祖”。
曾幾的观点显然受到吕本中《宗派图》的影响,并且强调杜甫对江西诗派的影响,开方回“一祖三宗”说之先声。
南宋诗坛上,江西诗派这个概念被普遍接受,一些人还在吕氏《宗派图》的基础上补添他们认为应该属于该派的作家。如赵彦卫《云麓漫钞》将吕氏本人列入派中,刘克庄又将曾幾归属该派(见刘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七《茶山诚斋诗选》),严羽《沧浪诗话》认为陈与义“亦江西之派而小异”。
又南宋淳熙年间程大昌刊刻江西诗派总集,诗人杨万里为其作序,并提出认识江西诗派“以味不以形”的重要观点。其后,刘克庄又作江西诗派总序和派中各家的小序,第一次对江西诗派做了比较系统的评论。
宋末元初的方回选评《瀛奎律髓》,对江西派诗人推崇备至,提出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的说法。他还有老杜为祖,黄氏、二陈及吕本中、曾幾这五家为“诗之正派”的说法。上述的补添成员、刊刻总集、评论作家、确立宗祖,都是对吕氏《宗派图》的发展。

《瀛奎律髓汇评》
江西诗派在南宋诗坛的影响是很深入的,正因为这样,给我们确定该派的成员和它的存在时期带来一定困难。考虑到“诗派”的应有涵义,我们还是综合采取上述南宋诸家的观点,认为江西诗派是存在于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的一个诗歌流派。

要研究江西诗派的形成原因,我认为首先应该着眼于宋诗发展的整个历程,尤其要了解元丰、元祐时期的诗歌创作高潮与元祐之后诗派产生的内在关系。
从总体上看,宋诗渊源于唐诗,但唐宋之间隔着一个五代十国时期。尽管我们今天研究文学史的人已经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部真正科学的文学发展史,在确定文学的发展、演变的阶段时,要尽可能从文学史自身寻找依据,而尽量排除其他的史学形态如政治史的外在形态(王朝更替等)的干扰。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像王朝更替这一类政治史或社会史的外在形态,其与文学发展并不仅仅只有一种外在的、并行的关系,而是在这类外在形态之下往往有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实质性变化,从而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家特别重视王朝、世运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虽然不排除有以王统、道统凌驾于文统之上的谬误意识,但也包含着对文学发展与历史发展关系的真理性认识。
像五代十国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间隔于唐宋两代之间,其对唐宋两代文学的承变关系的影响,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纯粹的时间间隔,而是造成宋文学新起点的首要前提。何况五代时期自身也是一个有着一定相对独立性的文学史时期,它对宋文学也有影响。

《江西诗派诗传》
当然这个问题已经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我们只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五代是一个历史的大滑坡,尽管在这个大滑坡时期文化上仍有上升、发展的成果,但诗学和诗歌创作本身却确实是沿着晚唐以来的某些不佳态势继续滑易,成为诗史上的一个低谷。当然这里并不包括五代时期新兴曲子词。
因为这个原因,促使宋代诗人产生这样一种观念,走出五代时期的低谷,跨越它,追求与唐代诗歌接武。对于前期的晚唐体、西昆体、白体等流派的诗人来说,似乎还没有明确地形成在唐诗之外另创有宋一代诗歌的意识,所以只满足于重现某类唐诗的风格。
自觉创造宋诗时代风格的创新意识是在北宋中期和后期出现的,从外在因素来看,它也是盛宋时期社会及文化的发展高潮促成的。庆历前后是宋诗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重要诗人。
这个时期的诗歌革新跟同时的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士人群体独立意识增强、政治革新等外在因素直接联系在一起。也正因为这些原因,这个时期的诗学和诗歌艺术文化的因素过于突出,而诗歌艺术自身的主题却相当程度地被忽视。
我们通常所说的宋人以理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为诗,从它们消极的一方面来看,最突出的表现就在庆历前后的诗坛上。从艺术风格、审美趣味来看,这个时期的诗歌革新,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唐韩、孟等人为代表的诗歌革新派在北宋诗坛的延续。说到底,仍然带有前期诗人以重视唐诗、形似唐诗为满足的意识。只是因为此期诗歌完全是新的文化素养灌输成的,所以其成就大大超越了前期。
这其中梅尧臣也许是个例外,他比同期其他诗人更自觉地摆脱了某些文化因素的干扰,更多地往诗歌艺术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探索。这也许正是后来黄庭坚、陈师道和其他江西诗派更多地接受梅尧臣的影响的原因。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而梅诗的清切、古硬、幽微等风格特征,及其“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写作原则,几乎完全被江西诗派所接受和发展。
宋诗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在元丰、元祐时期。它不仅是北宋诗歌史的高峰,也是中唐元和、贞元之后的又一诗歌盛世。其代表作家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这一阶段的诗人们,既最大程度地接受了自中唐以来诗歌革新的艺术成就,又对它进行了反思,自觉克服革新诗派在诗学观念和具体创作实践上的偏差。
同时,这一时期的诗人放弃了对唐诗进行局部模仿的作法,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唐诗领域,也广泛地吸取唐诗之前的诗歌艺术传统,采取融合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发展道路。这跟这时期的整个士大夫学术文化普遍追求“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境界是一致的。
苏轼赞王安石在思想和学术上能“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正反映这时期文化各领域代表人物的气魄。从诗歌领域来看,最自觉、最努力地走这一道路的正是江西派宗师黄庭坚。对此,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有精辟的分析:
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则又专为昆体,故优人有寻扯义山之诮。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后出,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磨,不易之论也。

《刘克庄集笺校》
但是,刘克庄没有意识到,黄庭坚荟萃百家、自成一家的艺术成就的取得,以及他之所以能成为江西派的宗祖,这些现象不能从黄氏个人那里寻找解释,而是要将黄氏的成就放在元祐诗歌高潮的整体中来考察其成因,从整个北宋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寻找黄氏诗歌艺术出现的某种必然性。
当然,这样说丝毫没有忽视黄氏个人的各种因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想指出这个简单的事实:黄诗的变体、创新的价值如何,是后世诗歌评论家们争执、歧异最多的一个问题,全面否定黄诗的学者,也不乏人在。
但是在黄诗产生的时代,黄诗是得到诗坛的广泛接受,是受到当时整个诗歌界的鼓励的。这反过来证明黄诗符合当时诗坛的整体倾向,当然也是后来江西派选择以黄诗为艺术典范的基本前提。
宋诗发展经过了庆历前后和元丰、元祐两个高峰,其时代风格已经形成,并出现了自身的诗歌艺术系统及典范作家。尤其是第二个高峰,使宋诗臻于全面的成熟。此后的诗人在艺术继承和发展上有了自己时代的立场和基础,可以通过同时代典范作家的艺术去认识、接受诗史。
而在元丰、元祐诗歌高潮之后,如何继承这一高潮的艺术成就,也是摆在元祐后登上诗坛的那一辈诗人面前的基本问题。高潮产生了站在艺术峰巅上的一些典范作家,高潮之后的追随者们不可能以比诸大家更大的才华和学殖、功力来融合诸大家,所以客观上只能走上各自选择艺术典范的发展道路。
元祐诗人苏轼、黄庭坚都是典范,陈师道虽然艺术上不及苏黄广博,但其在局部的精深造诣,也具有典范的价值。其他元祐诗人如张耒、晁补之、秦观等名家,在艺术上也有局部的典范价值。

《宋诗一百首》
从元祐以后的北宋末、南宋初,乃至整个南宋时期的诗坛情况来看,上述作家(当然还应包括王安石及欧、梅、苏)都曾在整体或局部成为后来诗人的效法对象。这正是南宋诗坛流派纷纭的一大原因。
无疑,至少从江西诗派的形成历史来看,我们可以说,黄庭坚和与他旨趣相近的陈师道,在元祐后到南宋前期这段时间内,在被选择作为典范这方面,频率最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已经是研究江西诗派产生的正面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出现江西诗派,是宋诗高峰之后、宋诗成熟之后的一个现象。这反映了文学史演变的某种规律,在文学流派的形成方面也有一定的典型性。
假如从继承前人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说,黄庭坚和其他元祐大家的继承方式是融合式,而追随他的一些江西派诗人,则是“选择式”的,也表现了相当程度的模仿性。当然,这一派诗人有时也走上了另一极端,即为了求自立,放弃了对古人和前辈典范作家的继承,走向艺术上的滑易和率浅,局部地方重蹈了五代、宋初诗风中的陋习。

江西诗派的宗师黄庭坚,自少就学习诗歌创作。治平四年(1067)进士及第,是他的仕途之始,也是他正式走上诗坛的标志。他自己后来追述创作经历时也说“诗非苦思不可为,余及第后始知此”,可以说这是他走向成熟风格的创造的第一次“顿悟”。
在这之后的整个熙宁、元丰时期里,他广泛地研摹古人之作,也吸取北宋诸家的艺术经验,体兼正变、思合奇常,逐渐形成他自家的艺术风貌。这时期他逐渐进入当时最有影响的诗人群体之中,在审美趣味、风格形式上积极接受群体的影响,与苏轼及苏门其他诗人在创作上形成竞出并秀之势,当然也沾染了当时诗坛上的一些不良习气,如片面追求奇与难、强押窄韵等。
元祐时期是黄氏在艺术上完全成熟的时期,他的一些在章制和语言风格上创新色彩显著的作品,被苏轼第一个呼为“庭坚体”(详见《山谷内集》中《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一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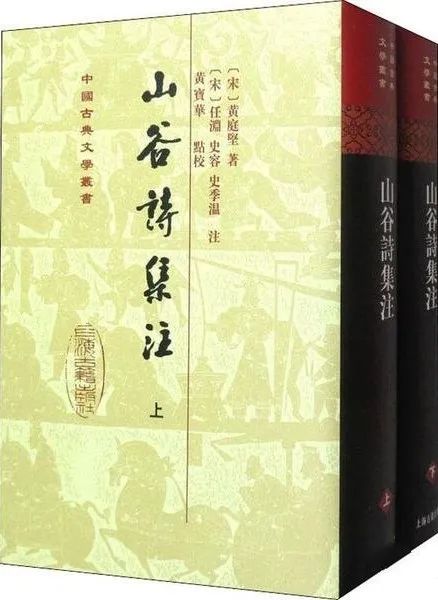
《山谷诗集注》
“庭坚体”被苏轼等成名作家“戏效”,也开始成了青年诗人研摹取法的对象。而陈师道则以成名作家的资历明确表示要学习黄诗,其晚年所作《答秦觏书》云:
仆于诗,初无师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
陈氏所说的这件事,发生在元丰末。尽管陈氏的功力和成就非“学黄”或“学杜”可以概括,但他确实很认真地学习黄诗,尤其在七古、七律诸体上,吸取黄诗章法曲折、词气瘦老的作法。后来当他自己也成了一些青年诗人取经、效法的对象,他仍然一贯地向其诗弟子宣传黄诗的好处。
如江西派中的重要诗人晁冲之,就是后山的传人,还有黄预、魏衍等徐州一带的诗人,虽无作品,但据陈师道与他们的唱和诗可以肯定,也是以黄、陈为宗的。
“黄庭坚体”的成熟,为江西诗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诸家的仿效,可以看作是后来江西诗派的滥觞,也显示诗派产生的必然性。
元祐以后,黄庭坚在诗坛上的地位迅速提高,在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成长的一些诗人,开始在诗坛上崭露头角。在向他们传授诗学的过程中,黄氏也总结了他的诗学理论,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诗学见解,尤其是提出诗歌艺术与人格修养、学术积累的关系,诗歌创作中的法度和自然、尚奇与平淡等方面的关系,以及追求“兴寄高远”的美学原则,对于江西派的形成,有理论上的奠基意义。
不仅如此,黄氏还经常跟后辈诗人讨论创作上的许多细节问题,引导他们体会风格,追寻章法、句法及炼字法。这方面的材料不少,散见于南、北宋时期的各种论诗著作中。

《宋诗话全编》
现略引《王直方诗话》所载数例:
潘淳字子真,南昌人也。尝以诗呈山谷,山谷云:“作诗须要开广,如老杜‘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之类。”子真云:“淳辈那便到此。”山谷曰:“无此只是初学诗一门户耳。”
山谷论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
山谷谓洪龟父云:“甥最爱老舅诗中何等篇?”龟父举“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及“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以为绝类工部。山谷云:“得之矣。”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窥见黄氏日常传授诗学、诗法的情形。前面我们提到过江西诗派为何选择黄庭坚作为宗师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从多方面寻找原因,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黄诗强调了法度,强调了作家在创作中的理性省察,为学习者提供了门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黄氏晚年的诗学传授活动,尤其是他所采取的这种既重视诗学基本原则,又对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细腻分析的传授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将苏黄二人稍做比较就可清楚,苏轼在元祐诗坛的地位高于黄庭坚,他的诗歌也是包括江西派诗人在内的诗坛后进的学习对象,苏氏发表论诗见解也不少。
但是跟苏诗的风格以自由抒发、肆其天才笔力的作法相似,苏氏的诗学见解也是主张自由体验的。苏黄二人在美学思想上也有许多接近一致的地方,但苏氏的议论一般只停留在原则的提出、风气的崇尚这一层次,所以具有美学思想的价值,而能落实在具体创作活动上的东西比较少。

《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
黄庭坚不仅揭示原则,还构建了具体的创作理论,自然比苏氏诗学更多了一种可行性,其对后学的吸引也就更大些。
在黄氏晚年,诗派已经有些端倪。黄氏自己对此似乎也有所觉察,其《书倦殼轩诗后》一文中提到了潘邠老、“二何”、“四洪”、徐师川、潘子真这九位与他直接有交往的后辈诗人,认为他们“皆可望以名世”。
在另外一些场合,他也褒扬了不少后辈诗人,如王立之、高荷等人。同样,陈师道则褒扬过晁冲之、韩驹等人。这些人都是吕本中《宗派图》中的主要成员。禅宗重宗派,宋学重师承,江西诗派形成的外部文化原因中,正有这两方面。当然吕氏之后的许多论家对于江西诗派的理解,已经完全突破直接的师承关系这一点,所以才有将曾幾、吕本中、陈与义等家纳入诗派的作法。

江西诗派是一个重视诗歌本位,重视诗歌艺术传统的诗派,因此它的理论侧重于阐述诗歌艺术的本质和一些创作上的规律性的东西,而这种“本质”和“规律”,是通过深入地研摹古人作品、广泛地接受诗史的启示而体认、摸索出来的。
我们知道,我国文学史上有不少以复古为宗旨的作家和流派,还有模拟古人作品的拟古作法。严格地说,江西诗派的提倡学古与一般的复古派有本质的区别,一般的复古派或提倡恢复古代的艺术精神,或仿效古代典范作品的艺术风格,其意识上有明显的怀念他们心目中过去的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试图回归过去的倾向。
而江西诗派的学古则重在从古人那里吸取丰富的艺术经验,尤其强调从“法度”这一角度去学习古人。他们认为,学习创作首先应该研摹古人的作品,以古人作品为典范。黄庭坚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如《与王立之》云:
若欲作楚词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词,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然后下笔。譬如巧女文绣妙一世,若欲作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尔。
又其《与元勋不伐书》云:
如欲方驾古人,须识古人关捩,乃可下笔。
又如其《答王子飞书》论陈师道的诗文创作云:
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

《黄庭坚全集》
以上黄氏所说的“用意曲折”“关捩”“关键”,正是“法度”的近义词。他不直接说“法度”,而用了这些比较形象、生动的说法,是为了让学诗者更好地体验创作中法度运用的活境。
对该派诗人来说,“法”并非纯粹抽象的东西,更不能理解为机械性的操作规则和操作工具,而是指整个创作活动中存在的创作者的理性省察、反思的那一方面思维活动,是指创作中的意识性活动。
从这一点上说,江西诗派是一个十分重视创作中的理性活动的诗派,也可以说是一个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艺术流派,与强调创作活动的激情作用、无意识作用的浪漫主义诗学、直觉表现主义诗学有明显的差别。
当然,这种差别是相对的,江西诗派对创作活动的本质的认识,绝不仅仅只是强调法度理性之一元,而是充分认识到创作活动中的直觉色彩、无意识的那一部分,也充分认识到法与具体的境界的关系。
这就是在“法度”外又提出“神”“活法”等概念,从而使江西派的诗学思想带有比较充分的辩证,使它赢得了能够指导具体创作实践的功能。这也是该派之所以能成为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两方面能平衡发展的诗歌流派的原因。
江西诗派不仅重视“法”,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对“法”的超越问题,主张法随境生,法与具体的立意结合。
黄庭坚认为“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后来陆游《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云“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正是对黄庭坚上述思想的发展。
就总体的倾向来讲,大部分江西诗派的诗人,都很重视真实的境界、真实的感受对诗歌创作的必要性,而且江西派诗人在意境塑造方面的成就也是很突出的。该派的佳作,不仅有拗硬、瘦健等独特风格,而且意境情韵也都好。

《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
如下述作品:
黄庭坚《登快阁》: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陈师道《秋怀示黄预》:
窗鸣风历耳,道坏草侵衣。
月到千家静,林昏一鸟归。
冥冥尘外趣,稍稍眼中稀。
送老须公等,秋棋未解围。
韩驹《夜泊宁陵》:
汴水日驰三百里,扁舟东下更开帆。
旦辞杞国风微北,夜泊宁陵月正南。
老树挟霜鸣窣窣,寒花垂露落毵毵。
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共蔚蓝。
这些诗歌,都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各家在句法、章法、立意、运思等方面的个人作风,但是感受都很真切,意境能够创新。从这里我们不难领悟江西诗派诗人们在处理法与境界、法与立意等关系的独特匠心。又如江西诗派在具体句境创造方面经常借鉴、化用前人的名句,甚至提出了“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名目,这方面确实暴露了某些弊病,乃至限制了该派诗人在诗歌语言创新方面的成就。
但是,在许多作品中,江西派诗人都成功地运用这类手法,创造出与前人不同,甚至韵味胜于前人的名言、警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诗人虽是借鉴前人的选境立意方式,但自身的创作同样是植根于丰富充沛的感受状态中,同样有灵感的闪现。

《冷斋夜话》
如惠洪在《冷斋夜话》中举为“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的“换骨法”例子的黄庭坚题达观台诗,在境界创造上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感受和观察事物、表现事物的敏锐眼神。全诗如下:
瘦藤拄到风烟上,乞与游人眼豁开。
不知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
惠洪认为后两句借鉴李白“鸟飞不尽暮天碧”“青天尽处没孤鸿”而作,其实《望岳》“决眦入归鸟”句也与此类似。推而言之,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其造境方式也属此类。
但黄氏只是借鉴了前人的某些东西,其感受则是眼前所生,是王夫之所说的“现量”。这种例子在江西诗派作品很常见,本书在有关诗句的赏析中都已点出。前人诗话中评赏该派作品,也不乏这方面的分析。如陈长方《步里客谈》有云:
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花诗亦用此体,云“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至陈无己云“李杜齐名吾何敢,晚风无树不鸣蝉”,则直不类矣!
陈氏所论之法,富有禅意,通过转化关注对象、移易境界以打断前面的情感流程,达到“超脱”的境界,亦如禅家之断“常见”而入禅思。
黄氏的诗句虽借鉴杜句,甚或借鉴禅的表达方式,但有自己新鲜的感受,与杜句一样能做到新奇而又浑成,所以是成功的。而陈师道的这两句诗虽未为顽劣,但毕竟用意太刻露了一些,“法”的痕迹太明显,缺乏当下直刻的真感受。
又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所举一例,也很能说明这个道理:
外祖晁君诚善诗,苏子瞻为集序,所谓“温厚静深如其为人”者也。黄鲁直常诵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听羸马龁残蔬”,爱赏不已。他日得句云:“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自以为工,以语舅氏无咎曰:“吾诗实发于乃翁前联。”余始闻舅氏言此,不解“风雨翻江”之意。一日憩于逆旅,闻旁舍有澎湃鞺鞳之声,如风浪之历船者,起视之,乃马食于槽,水与草龃龊于槽间而为此声,方悟鲁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适相遇而得之也。

《石林诗话》
这一段分析很细致,最后所得的结论也很合理。山谷此两句虽受晁君诚的启发,然意趣、词气都不同于晁诗,境之造奇更与晁诗之平易清新有别。但叶氏通过生活中的亲身体验,肯定了黄诗在感受上的真实性,认为它不是单纯“意索”而得,而是情景相接,自然触发而成。
这类例子很多,不烦赘举。总之,江西派所说的“法”,从其积极的、有价值的一面来看,始终没有离开“意”与“境”。这派诗人在表现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方面,同样作出了多方面的建树,内容上更有许多开拓,并非像有些论者所诟斥的那样,只知从书本中讨生活。
黄庭坚还提醒后学,不要因拘守法度而妨碍了个人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和独特风格的创造。其《与洪驹父书》就阐述了这一观点,其中云:
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俭陋也。
苏轼有一论艺名言,叫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黄庭坚的这番议论,与苏氏论艺的旨趣最接近。
不仅如此,黄氏还从而提出“入神”“大巧”等概念,进一步深化对“活法”及其作用的辩证认识。其《赠高子勉》诗云“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又《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惠次韵奉酬四首》云“覆却万方无准,安排一字有神”,又《次韵奉答文少激纪赠二首》云“诗来清吹拂衣巾,句法词锋觉有神”,都明确地强调创作上的入神境界。
江西诗派的诗人,在黄庭坚的认识基础上,根据各自的领悟,提出了各人的创作要义。
曾季貍《艇斋诗话》对此有所概括,云:
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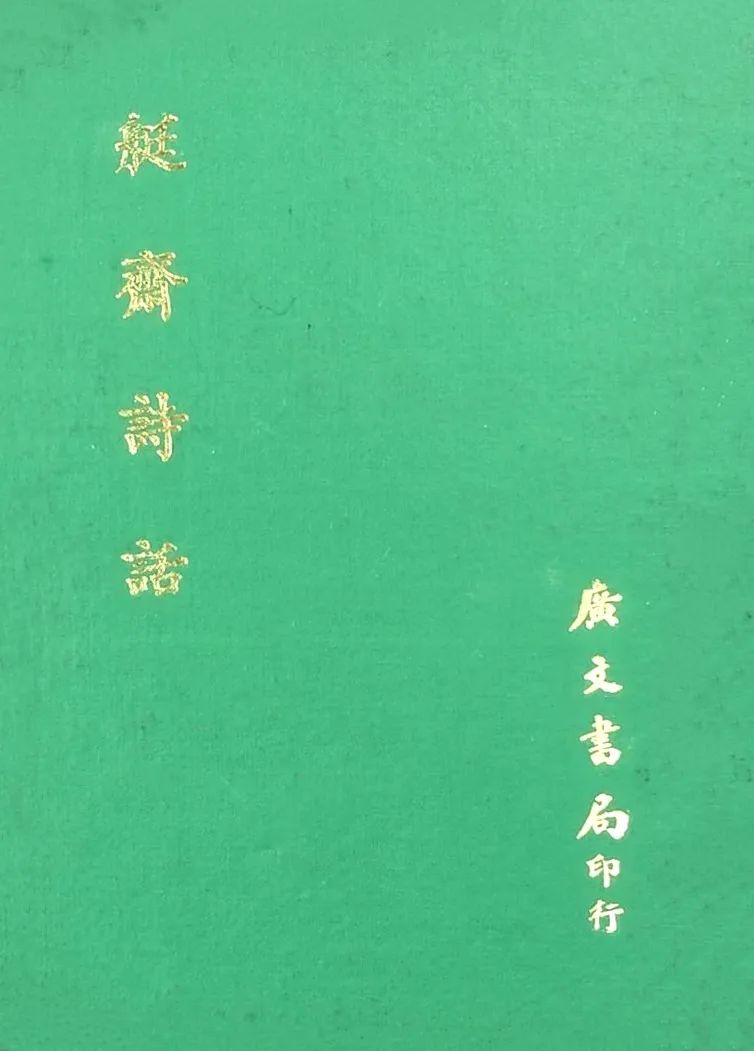
《艇斋诗话》
曾氏所说“悟入”,其实是指对诗的创造本质、诗歌表现中的艺术规律的领悟。这里存在着飞跃、顿悟的机制。其中吕东莱的“活法”,比较简捷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成为后期江西派诗学的代表性观点。
吕氏在《夏均父集序》中提出了“活法”这个概念,其文云: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
东莱“活法”是他在诗学上的最大心得,平生常形于笔端,如“胸中尘埃去,渐喜诗语活”(《外弟赵才仲数以书来论诗,因作此答之》)、“笔头传活法,胸次即圆成”(《别后寄舍弟三十韵》)、“文章有活法,得与前古并”(《大雪不出寄阳翟宁陵》)。
江西派另一位诗人谢薖《读吕居仁诗》也说吕氏“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活法”的提出,对江西诗派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它破除了前期许多江西派诗人死板地揣摩黄、陈等人的法度,在外在形式上追求与黄、陈形似的作法,为后期江西诗派诗人在风格上的创新变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启迪。可以说,它透露了南北宋之际诗风演变的某种契机。
“活法”的含义很丰富,用典使事、写景抒情、结构机轴,处处皆有活法可言。从江西诗派的观点来看,诗中见活法,就是其成功的标志。至于何等境界方才称得上是“活法”,则需要作者和读者自己领会体悟。
南宋人陈模《怀古录》卷中曾论到“使事”方面的活法,举了陈与义《和张规臣水墨梅》、东坡《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等作品,认为都是“使事而得活法者也”。味其大意,是指这些作品在咏物时能运用不相干的典故来形容,从而得到新奇活络的效果。

《江西诗派研究》
中晚唐人咏物多用本典,其甚者至于完全像在搬抄类书,宋人咏物则多用不相关之典,从中寻求新的意义,确定新的关系。至于白描写景咏事,也有活法可言,南北宋之际的诗人陈与义、吕本中、曾幾、徐俯等人都有写景活泼生新、机趣流露的作品,开后来杨万里一派的诗风。本书在有关作品的赏析中都论到具体创作过程中的“活法”表现,兹不赘述。
江西诗派强调诗法,并对其作种种的辩证阐述,从根本上说,正体现了该派对诗歌艺术本体的充分重视。
自中唐以来的诗歌革新思潮,是以社会文化的整体革变为一重要的外部促成条件的,也正因为这样,社会文化方面的主题曾经相当程度地侵扰诗歌自身的主题,造成诗的本体意义被淡化、诗与其他的文化形式及文学体制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的现象。
元祐诗坛对上述“非诗化”倾向作了相当大的纠正,黄、陈等人又提倡诗法,以从理论上重新确立诗的本体和本位。江西诗派正是沿着这一基本趋势发展下去。当然,这种趋势也导致了另一些不足,如江西派后学作品题材过于狭窄、诗的社会功能明显降低,以至走上了纯诗化、形式化的道路,等等。
但这些不仅是因为艺术观念,也跟元祐之后的政治形势有关系,它促使诗人精神上的过度内向、收敛,从而失去了盛宋时期发扬蹈厉、恢弘广大的气象。

《中国诗学的关键流变:宋代“江西诗派”》

上面就江西诗派的概貌、成因及其基本的诗学主张做了 一些论述性的介绍,最后想就本书的撰述问题做些交代。
鉴于本书的宗旨是要标揭流派的品格之作,所以在选目上突出大家和名家,兼及小家。江西诗派的大家有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他们在整个诗史上也是居于杰出作家之列。名家如韩驹、吕本中、曾幾等人,也都有足以自立的地位,是宋诗发展中起到一定作用的作家。
大家与小家之间,在艺术成就方面客观上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也是江西诗派发展中的一个实际情况,即这个流派不是因一群才力相若、主张相近的诗人组成的,而是在一两位大作家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与黄、陈师承最明确、关系最接近的那些嫡传弟子,艺术上的成就都不算很高。而与黄、陈距离较远,甚至只是私淑性的传承关系的一些诗人,反而有更高的成就,其中陈与义就是杰出的代表。
由于出现这种现象,无怪乎南宋及金、元人对宗派传承的风气提出质疑。其实有些派中人也看到这个缺点,如吕本中认为:“《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就是针对派中人专知宗法黄、陈和杜诗,门户自守的现象而发的。

《江西诗派诸家考论》
在选录作品方面,本书以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为基本依据。我认为一个流派中艺术成就最高的那些作品,就是该流派的品格。
江西诗派是一个由正入变,亦正亦变的诗歌流派,即以绝句一体而论,江西派诗人基本上都是正、变两种风格都擅长,都有佳作。当然更多的佳作是正中有变、变仍近正,这正是江西诗派的成功奥秘,也是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
本书选录的大量优秀作品,能证明笔者的这个看法。而阐述艺术创作上的正变之际的关系,尽可能将一些作品纳入一定的诗史传统中去理解,也正是笔者在赏析方面的致力之处。
江西诗派提倡兴寄高远、含意幽微,这是对中晚唐以来浅露暴见诗风的一个革新。如任渊说“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话虽说得有些玄乎,但情况确实是这样。
该派即使在写景状物方面,也反对浅露,倡深微复远,象中有象,象外有意,以一景摄多景,一事映多事。陈师道的诗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在这方面,本书力求既不穿凿,又不和光同尘、以不求甚解为高,以致汩没古人的良苦用心。
其余撰写宗旨,前面在论江西诗派的成因、诗学主张时,实际已经谈到了许多。读者可以将前言所论和有关具体作品的赏析文字参互阅读,即可对笔者所论作出或是或非的评价。
江西诗派是一个文化色彩比较鲜明的流派,它受整个北宋及南北宋之际的思想、社会文化、政治背景的影响很是深刻。
对此,本书在一些文化色彩、文化主题突出的作品中有一些集中的论述,如该派诗与党争背景、禅学及理学思想、书法、绘画等文化因素的关系,都有所论述。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但是,诗歌艺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诗无疑是受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但从社会文化背景到诗歌艺术,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探讨这些问题,需要运用整体性、专题性的研究方式。有些问题在一个具体作品的赏析过程中无法完满解决,弄不好还会有横生歧见、穿凿附会的毛病出现,所以本书在这方面是以尽量稳重为宗旨的。
本书在鉴赏批评的方法上,一方面尽可能发掘传统诗学中的一些有价值的鉴赏、批评方法;另一方面也可能运用现代的美学观念和诗歌鉴赏批评方法。期望能做到唯适是用,不以门户限,不以古今限。
江西派诗人擅长用典使事,善于化用诗赋及经史百家中语。这方面,若无历来注本的不断索解、不断累积,以个人之力,即便穷研其中一位大家或名家,恐怕都要穷年连载的努力。在这方面,自南宋以来的有关注本、选注本为笔者提供了很多便利。
鉴于选注一类书的性质,在具体参考中不烦注明。有些纯属注家个人发现的地方仍注出。赏诗品文,各人的审美心理有同有异,各有所得,有时也难免各执一端,不解通融。笔者本着同所不能不同、异所不能不异的宗旨,在解释方面难免有得有失,期待海内外方家赐予批评!

《朝鲜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

钱志熙(1960—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选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学术部主任,《国学研究》编委等。著有《唐诗近体源流》《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