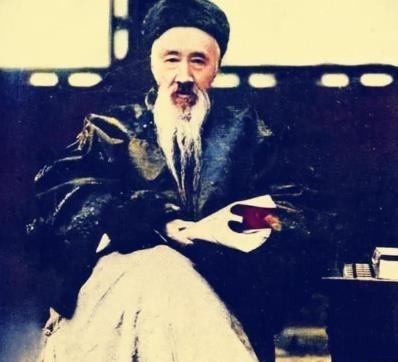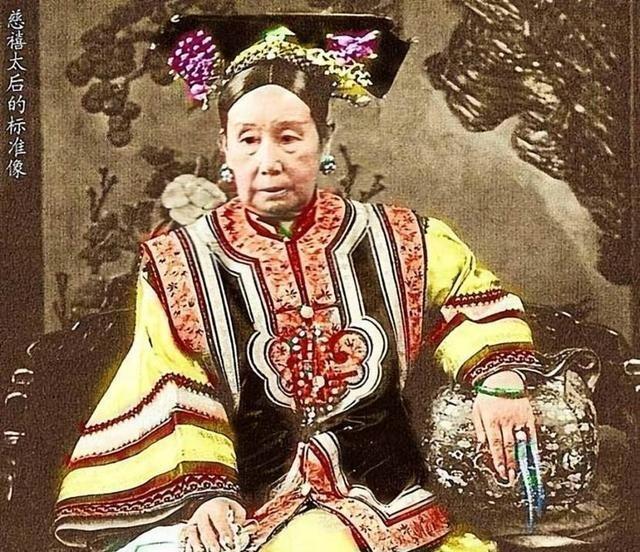1735年10月8日深夜,57岁雍正突然死在距京20公里的圆明园,从得病到死亡,就一天时间,事出突然,群臣毫无准备,园内乱成一锅粥,不是因为皇帝死了悲伤过度,而是册立新君的诏书找不到了。 圆明园的夜格外静。深秋的凉气透过殿宇的缝隙往里钻,烛光在风里轻轻晃。 雍正还在批阅奏折,案上堆着一摞又一摞的文件。 谁都没想到,这会是他亲手批的最后一批奏章。 雍正,爱新觉罗·胤禛,康熙第四子,45岁登基,在位13年。这人是出了名的“工作狂”,每天睡不到四个时辰,一年就给自己放三天假,奏折上的朱批加起来能有几百万字。他推行摊丁入亩、改土归流,把康熙晚年松弛的吏治狠狠收紧,朝堂上骂他“刻薄”的不少,可国库实实在在鼓了起来。 弘历,雍正第四子,也就是后来的乾隆,这年25岁。早在几年前,雍正就用“秘密立储”的法子,把他的名字写进了传位诏书,只是除了皇帝自己,没几个人敢打包票到底是谁。 张廷玉,康熙朝就跟着干活的老臣,汉臣里的头一号,雍正最信任的人之一,连秘密立储的规矩,都是他陪着雍正定下的。 鄂尔泰,满臣里的重臣,从云南巡抚一路做到保和殿大学士,手里握着军权,雍正临终前特意召他来圆明园,就是怕出事。 那天后半夜,雍正突然在“九州清晏”殿里喊疼。 伺候的太监李德全刚给皇上换了杯热茶,就见雍正捂着胸口从椅子上栽下来,嘴里“嗬嗬”地出气,手里还攥着那份没批完的奏折,朱笔在黄绫封面上划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红痕。 “快传太医!快传张大人、鄂大人!”李德全的嗓子都喊劈了。 太医们提着药箱往殿里冲,可雍正的脸已经憋得发紫,脉搏弱得像游丝。折腾到天快亮,一个老太医颤巍巍地跪下来,对着涌进殿的大臣们摇头:“回……回各位大人,皇上……龙驭上宾了。” 殿里瞬间炸开了锅。 有哭的,可更多人是慌。大学士张廷玉头发都白了,却比谁都镇定,他抓住李德全的胳膊问:“传位诏书呢?皇上说过,一份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份随身携带,你见过吗?” 李德全懵了,手忙脚乱地翻雍正的寝宫,龙袍的夹层、枕头底下、书案的抽屉,翻了个底朝天,连个纸片都没找到。 “找不到啊张大人!”李德全带着哭腔,“奴才伺候皇上这些年,从没见他把什么诏书带在身上!” 鄂尔泰在一旁跺脚:“乾清宫离这儿20多里地,现在去取?万一有人趁机作乱怎么办?” 可不是嘛。雍正的儿子里,三阿哥弘时一直憋着劲想争位,八爷、九爷的余党在暗处盯着,这时候找不着诏书,别说新君继位,怕是京城都要乱。 群臣你看我我看你,有人偷偷往殿外溜,想给自家主子报信,被张廷玉一眼喝住:“谁也不准动!皇上尸骨未寒,谁敢乱了规矩,按谋逆论处!” 他这话带着杀气,没人敢再动。 张廷玉闭着眼想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皇上去年跟我说过,随身那份诏书,藏在‘御笔’的锦盒里!就是他天天带着的那支紫檀木笔!” 李德全赶紧去翻雍正的书案,果然在一个刻着龙纹的锦盒里,摸出个黄纸包着的小匣子。 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传位诏书,朱砂写的“传位于皇四子弘历”几个字,盖着雍正的御宝,红得刺眼。 张廷玉捧着诏书,声音都在抖:“快请四阿哥!” 弘历这时候正在圆明园的别馆里守孝——他生母刚去世没多久。接到消息赶来时,一身素服,脸上挂着泪,却没忘了先给雍正的遗体磕三个头。 等他接过诏书,张廷玉带头跪下:“臣等参见新君!” 鄂尔泰跟着跪下,大臣们哗啦啦跪了一片,刚才还乱成一锅粥的殿里,总算有了点秩序。 可没人注意,弘历接过诏书的手,悄悄在袖子里攥成了拳。 后来,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那份诏书也取来了,内容一模一样,弘历的皇位算是坐稳了。 只是雍正的死因,成了个谜。 有人说是累的,毕竟13年没好好歇过,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 有人说是吃丹药吃的,雍正晚年确实在圆明园里养了帮道士,炼丹炉没断过火,丹药里的铅汞超标,说不定就是催命符。 还有人说是被仇家害的,民间不是一直传“吕四娘刺雍正”的故事吗?虽然没实据,可也透着人们对这位“铁腕皇帝”的复杂心思。 弘历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炼丹的道士全赶走,还下旨说“先帝只是让他们做做样子,从没吃过丹药”。这话越解释,越让人觉得有猫腻。 但不管怎么说,雍正用“秘密立储”这招,总算没让权力交接出大乱子。要是还像康熙晚年那样明着争储,他突然一死,大清怕是真要内讧了。 只是想想那个深秋的夜晚,雍正倒在奏折堆里,手里还攥着朱笔,而群臣最慌的不是他的死,是找不到那份决定江山归属的纸,就觉得帝王家的凉薄,比圆明园的秋霜还寒。 信息来源:《清世宗实录》《张廷玉年谱》《清史稿·世宗本纪》《大义觉迷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