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小说,自然不能与现实或历史直接等同。无论其中有多少人物、事件有历史原型,这些人物、事件一旦作为素材进入小说,就与历史原型再无关涉,而是构建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是解读小说的基本立场。

《读奇书,论奇人:水浒人物揭秘》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说,任何小说都不可能只是孤立地讲述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其中往往有着经过变形的现实或历史的投影。具备多义性的文学名著更是可以让人浮想联翩。
故此,即便基于《水浒传》现有文本解读梁山人物,也能够得出许多耐人寻味的关于现实或历史的感想与结论。
《水浒传》中,“双鞭”呼延灼出身名门,为北宋开国名将“铁鞭王”呼延赞嫡派子孙,入伙梁山前为汝宁郡都统制。对梁山人物而言,都统制是相当耀眼风光的职位。梁山接受招安后,先后立下征辽、征方腊两次大功,生还的多数天罡星将领也不过是受封都统制。
呼延灼久经军旅,“使两条铜鞭,有万夫不当之勇。……手下多有精兵勇将。”(第五十四回,727页)[1]
梁山一流战将包括“马军五虎将”、“马军八骠骑”前几位及鲁智深、武松等“步军头领”,呼延灼是梁山一流战将中与梁山人物交手最多的一位。梁山人物排座次时,呼延灼上应“天威星”,排名第八位,名列“马军五虎将”第四位。
相比“霹雳火”秦明的爆发力与冲击力,呼延灼更有谋定后动的统帅之才。呼延灼与“青面兽”杨志同为名将后裔,虽然不像《杨家将》、《呼家将》[2]等家将小说中的杨延昭、杨宗保、呼延庆等名将后裔那样享有主角光环,却都是承载历史意识的梁山人物。
一、呼延灼的梁山排名主要仰仗自身的武艺与地位,而非祖上的赫赫威名
宋末元初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赞》中,有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名单,“铁鞭”呼延绰排名第十五位,赞言写道:“尉迟彦章,去来一身。长鞭铁铸,汝岂其人?”[3]
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呼延绰在三十六人中排名第三十二位。“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投降海贼李横等出师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其呼延绰却带领得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降宋江为寇。”[4]呼延绰正是呼延灼的人物原型。[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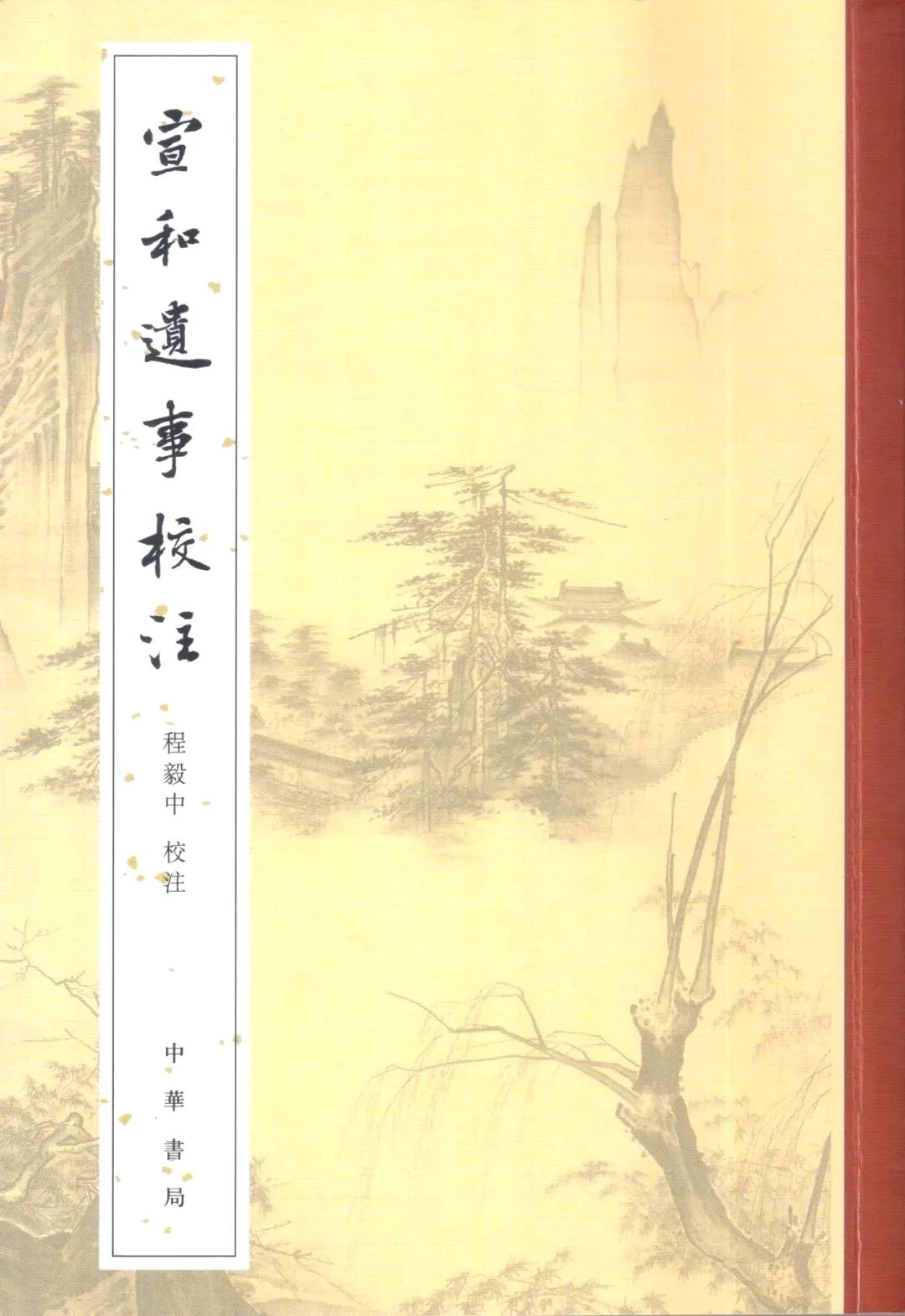
《宣和遗事校注》,程毅中校注,中华书局2022年3月版。
在早期的水浒故事中,呼延灼并未确定为呼延赞嫡派子孙,比拟的反倒是隋末唐初名将尉迟恭和五代后梁将领王彦章——准确地说,是使用铁鞭的民间形象,正史上的尉迟恭和王彦章的兵器分别是槊和铁枪:“(尉迟恭)善解避矟(槊),每单骑入贼阵,贼矟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矟,还以刺之。”[6]“(王彦章)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佗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7]
传世的元杂剧水浒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呼延灼作为梁山好汉只是提及姓名,并未展示出身、外貌和武器。《水浒传》中将呼延灼确定为呼延赞嫡派子孙,与呼延灼相斗的“病尉迟”孙立则被比拟为尉迟恭。
呼延赞是北宋将领,以勇武著称,宋太祖赵匡胤提拔于军旅之中。宋太宗赵光义擢升他为铁骑军指挥使。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呼延赞随同宋军征讨北汉,两军战于太原城下,他身先士卒,四次从城上坠下,负伤忍痛继续登城。

石湾瓷呼延灼
呼延赞还颇守为将本分。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呼延赞随同宋真宗赵恒巡幸大名。补选军校时人人叙说功劳,喧哗争执。呼延赞上奏道:“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无以报国,不敢更求迁擢,将恐福过灾生。”“再拜而退,众嘉其知分。”[8]呼延赞“遍文其体为‘赤心杀贼’字,至于妻孥仆使皆然,诸子耳后别刺字曰:‘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9]
正史上的呼延赞一脉,并非呼风唤雨的高官权贵,却是名副其实的勇将之门。在《杨家将》、《呼家将》等小说及传说中,呼延赞一脉地位显赫、绵延数代,忠勇爱国却惨遭奸臣陷害、杀戮。论及风光程度,也只有杨家将可以凌驾其上。
根据专家考证,呼延灼的历史人物原型的灵感来自于呼延赞,另有部分来自南宋“中兴四大将”之一韩世忠麾下将领呼延通。《宋史》未为呼延通立传,《高宗本纪》及《韩世忠传》中出现过他的名字。
不少杂史中也有相关记载。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关于呼延通生擒金国将领牙合孛堇一段写道:
(呼延通)驰至阵前请战,金人出猛将曰牙合孛堇,呼令通解甲投拜。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呼延太保在祖、宗时杀契丹立大功,曾设誓不与契丹俱生,况尔女真小丑,侵我王界,我岂与尔俱生乎?”即持枪刺牙合孛堇。牙合孛堇与通交锋,转战移时不解,皆失仗并马,以手相击,各抱持不相舍,去阵已远,于是皆坠马于坑坎中,两阵皆不知。牙合孛堇取篦刀刺通之腋流血,通搦牙合孛堇之喉,气欲绝而就擒。得官军百余相会,遂回,金人退去。[10]

《三朝北盟会编》
这段记载与梁山三败高俅期间呼延灼与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保的相斗经过颇为相似。呼延通自报家门“我祖呼延太保”,呼延太保即呼延赞。这是呼延灼的历史人物原型部分来自于呼延通的有利证据。
关于呼延灼与韩存保的相斗经过,《水浒传》中写道:
(韩存保与呼延灼)两个在阵前更不打话,一个使戟去搠,一个用枪来迎。使戟的不放半分闲,使枪的岂饶些子空。两个战到五十馀合,呼延灼卖个破绽,闪出去,拍着马望山坡下便走。韩存保紧要干功,跑着马赶来。
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约赶过五七里,无人之处,看看赶上,呼延灼勒回马,带转枪,舞起双鞭来迎。两个又斗十数合之上。用双鞭分开画戟,回马又走。韩存保寻思:“这厮枪又近不得我,鞭又赢不得我,我不就这里赶上捉了这贼,更待何时!”抢将近来,赶转一两山嘴,有两条路,竟不知呼延灼何处去了。
韩存保勒马上坡来望时,只见呼延灼绕着一条溪走。存保大叫:“泼贼,你走那里去!快下马来受降,饶你命!”
呼延灼不走,大骂存保。韩存保却大宽转来抄呼延灼后路,两个却好在溪边相迎着。一边是山,一边是溪,只中间一条路,两匹马盘旋不得。呼延灼道:“你不降我,更待何时!”韩存保道:“你是我手里败将,倒要我降你。”呼延灼道:“我漏你到这里,正要活捉你。你性命只在顷刻!”韩存保道:“我正来活捉你!”
两个旧气又起。韩存保挺着长戟,望呼延灼前心两胁软肚上,雨点般搠将来。呼延灼用枪左拨右逼,泼风般搠入去。两个又战了三十来合。正斗到浓深处,韩存保一戟望呼延灼软胁搠来,呼延灼一枪望韩存保前心刺去,两个各把身躯一闪,两般军器都从胁下搠来。呼延灼挟住韩存保戟杆,韩存保扭住呼延灼枪杆,两个都在马上你扯我拽,挟住腰胯,用力相挣。韩存保的马后蹄先塌下溪里去了,呼延灼连人和马也拽下溪里去了。
两个在水中扭做一块。那两匹马溅起水来,一人一身水。呼延灼弃了手里的枪,挟住他的戟杆,急去掣鞭时,韩存保也撇了他的枪杆,双手按住呼延灼两条臂,你掀我扯,两个都滚下水去。那两匹马迸星也似跑上岸来,望山边去了。
两个在溪水中都滚没了军器,头上戴的盔没了,身上衣甲飘零。两个只把空拳来在水中厮打,一递一拳,正在水深里,又拖上浅水里来。正解拆不开,岸上一彪军马赶到,为头的是没羽箭张清。众人下手活了韩存保。(第七十九回,1018-1019页)

王阅飞绘呼延灼
这是整体平庸的后半部《水浒传》中的精彩片章,对于彰显呼延灼的武艺大有裨益。在《水浒传》中以如此篇幅描写一次对战是相当奢侈的待遇,唯有梁山征辽期间孙立对战寇镇远一战可以相提并论。
“大刀”关胜与呼延灼同为名将后裔。关胜名列梁山武将之首,“武圣”关羽后裔的身份显然起了决定性作用。呼延灼的排名则主要仰仗自身武艺与地位,而非祖上的赫赫威名。
即是说,如果关胜抛开“武圣”后裔的身份,名列梁山武将之首将会更加名不副实,呼延灼抛开祖上的赫赫威名,排名当前位置仍然并无不妥。故此,对关胜名列林冲之前心怀不平之人不在少数,对呼延灼的排名却少有质疑。
二、以呼延灼的多次对战为联络点,可以用于勾勒梁山人物的武艺水准图谱
呼延灼领兵征讨梁山期间,以“连环马”大败梁山兵马,“轰天雷”凌振又以大炮助战,让梁山一度陷于苦战。
然而,呼延灼毕竟是以一人之力对阵整个梁山,虽说勇武过人、谋略不凡,终究力有不逮,先是副先锋“天目将”彭玘被扈三娘擒获,晁盖、宋江等人诱擒凌振。吴用又差遣汤隆、时迁及乐和下山,赚取“连环马”克星“金枪手”徐宁入伙,教授梁山兵马钩镰枪,而后大破“连环马”,呼延灼统领的朝廷兵马一败涂地,正先锋“百胜将”韩滔也被擒归顺梁山。

民国烟画《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呼延灼兵败后只身逃往青州。在青州慕容知府协助下,将桃花山的李忠、周通,白虎山的孔明、孔亮兄弟打得节节败退。李忠、周通向二龙山的“花和尚”鲁智深等人求救。与赶来救援的鲁智深、杨志过招时,呼延灼也是不落下风。孔亮前往梁山搬请宋江引军救援,吴用设计擒获呼延灼,经宋江好言相劝,呼延灼归顺梁山,又献计打破青州。
梁山聚义期间多次战败朝廷征讨兵马,呼延灼统领的朝廷征讨兵马是对梁山威胁最为严重的一次。这固然有赖于“连环马”作为特殊军种具备的强大杀伤力,呼延灼的善战之能与统兵之才仍然彰显无遗。
且不说虎头蛇尾、草率仓促的关胜领兵征讨梁山之役,梁山人物排座次后,朝廷先后派遣童贯、高俅领兵征讨梁山,虽说朝廷战将如云、来势汹汹,均未对梁山构成实质性威胁。双方数次交锋,梁山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朝廷兵马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至极。
朝廷征讨梁山之役几乎成了梁山人物单方面展示实力的舞台(当然,梁山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期间,战将与实力也远非呼延灼领兵征讨梁山期间可比)。
呼延灼领兵征讨梁山期间,梁山采取“车轮战”对战呼延灼:“霹雳火秦明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病尉迟孙立打第五阵。”
双方大战时,第一队“霹雳火”秦明出战,二十馀合斗得“百胜将”韩滔力怯,呼延灼刚要接斗秦明,第二队“豹子头”林冲赶到,说道:“秦统制少歇,看我战三百合却理会!”林冲挺起蛇矛,直奔呼延灼,双方大战五十合之上,不分胜败。

韩伍绘呼延灼
第三队“小李广”花荣赶到,大叫道:“林将军少息,看我擒捉这厮!”花荣挺枪出马,“天目将”彭玘出战,花荣二十馀合斗得“天目将”彭玘力怯,逼得呼延灼再次出战,斗不到三合,第四队“一丈青”扈三娘到,大叫:“花将军少歇,看我捉这厮!”
彭玘来战一丈青未定,第五队“病尉迟”孙立军马早到,勒马于阵前摆着,看这扈三娘去战彭玘。两个斗到二十馀合,扈三娘以红棉套索擒获彭玘。呼延灼看见大怒,忿力向前来救,扈三娘拍马迎敌。相斗十馀合,呼延灼狠狠一鞭望扈三娘顶门上打下来。扈三娘眼明手快,用刀一隔,呼延灼的鞭打在刀口上,扈三娘回马便走。
呼延灼纵马赶来,孙立见了,便纵马向前,迎住厮杀。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宋江看了,喝采不已。(第五十六回,731、732-733页)呼延灼逃往青州后,与鲁智深、杨志交手。
《水浒传》中写道:

连环画《大战呼延灼》
鲁智深在马上大喝道:“那个是梁山泊杀败的撮鸟,敢来俺这里唬吓人?”呼延灼道:“先杀你这个秃驴,豁我心中怒气!”鲁智深抡动铁禅杖,呼延灼舞起双鞭,二马相交,两边呐喊,斗四五十合,不分胜败。呼延灼暗暗喝采道:“这个和尚倒恁地了得!”两边鸣金,各自收军暂歇。
呼延灼少停,再纵马出阵,大叫:“贼和尚,再出来!与你定个输赢,见个胜败!”鲁智深却待正要出马,侧首恼犯了这个英雄,叫道:“大哥少歇,看洒家去捉这厮。”那人舞刀出马。……当时杨志出马来与呼延灼交锋,两个斗到四十馀合,不分胜败。
呼延灼见杨志手段高强,寻思道:“怎的那里走出这两个来?好生了得!不是绿林中手段!”杨志也见呼延灼武艺高强,卖个破绽,拨回马,跑回本阵。呼延灼也勒转马头,不来追赶。两边各自收军。(第五十七回,761页)
呼延灼对战的梁山人物中,秦明名列“马军五虎将”第三位,林冲名列“马军五虎将”第二位,孙立被许多人认为有“马军八骠骑”实力(甚至攻守兼备的作战风格和战功还高于部分“马军八骠骑”),扈三娘的武艺在地煞星中鹤立鸡群。
鲁智深的气力和武艺在梁山步将中独占鳌头,与“马军五虎将”相比并无逊色,杨志也公认有着不逊于“马军五虎将”的实力。呼延灼武艺的出类拔萃可见一斑,耐力也殊为惊人。他的统兵之才又是以上人物难以企及的。

剪纸双鞭呼延灼
与此同时,呼延灼的作战风格偏于防守型,即稳妥性有余,攻击性略显不足。这似乎也是呼延灼自出战以来,胜仗不少,败仗少有,战平之战更为多些的原因。
梁山“马军五虎将”中,呼延灼的作战风格与关胜、林冲相比,少了一些稳中取胜的洒脱,相比秦明、董平,又少了一些黑云压顶的狠猛。这是名将后裔出身及正规军旅生涯留在呼延灼身上的烙印。
关于梁山人物的武艺水准,卢俊义“一览众山小”的实力绝少争议:“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第六十回,801页)其他梁山人物及非梁山人物,对战战例及武艺展示程度各有不同,对其武艺水准的评判也是多有争议。
如果想要恰当评判梁山人物的武艺高低及排名先后,自然需要选取较为有效的战例作为依据。呼延灼先后与多名梁山人物有过对战,不同梁山人物之间又有过对战,或是与其他人物有过对战。故此,以呼延灼的多次对战为联络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于勾勒梁山人物的武艺水准图谱。
《水浒传》中,梁山人物排座次前的武艺和对战有着较为严格的标准,武将对战绝少超过五十回合,旗鼓相当的天罡星武将对战多是战至四五十回合不分胜负。天罡星武将对战地煞星人物多是十余回合,最多二十余合即可取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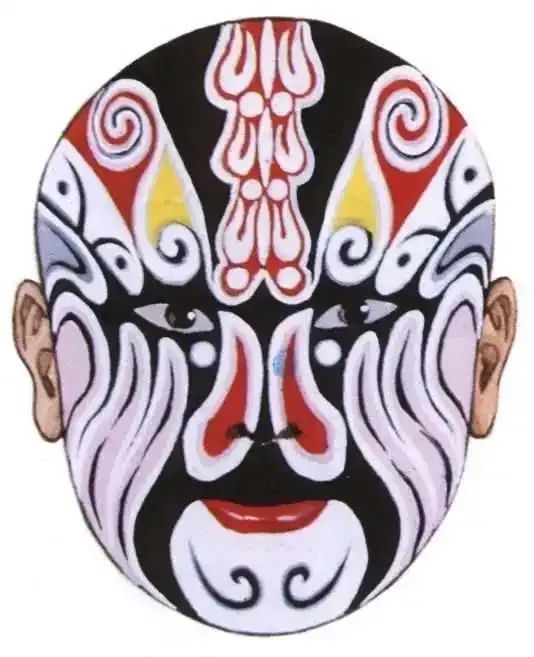
京剧呼延灼脸谱
而且,除了极少数梁山人物(如“九纹龙”史进),大部分人物出场后并无武力增长的状态。故此,梁山人物排座次前大体有着足以自圆其说的武艺体系。
“马军五虎将”在这个武艺体系中是巅峰般的存在。梁山人物排座次后,却多有超过五十回合的对战。梁山三败高俅期间,林冲大战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七八十合,不分胜负。(第七十八回,1013-1014页)
呼延灼大战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保一百回合以上,在张清等人协助下才得以活捉韩存保。(第七十九回,1018-1019页)
梁山征田虎期间,秦明与孙安大战五六十合不分胜负,次日,孙安与卢俊义大战五十余合,被战马颠下马来,换马与卢俊义再次大战五十余合。[11]
卞祥大战史进三十回合不分胜负,花荣爱其武艺高强,不忍暗箭射之,上前夹攻,卞祥力敌史进、花荣,斗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负。[12]
梁山征王庆期间,秦明与袁朗大战一百五十余合。[13]卢俊义与杜壆大战五十回合不能取胜,后与孙安联手杀死杜壆。[14]
以卢俊义的武艺定位,对战杜壆需要与另一位超级高手联手,杜壆的实力可谓是恐怖异常。
以此而论,如果杜壆对战梁山“马军五虎将”、“马军八骠骑”,不能说犹如老鹰搏小鸡,却具备绝对的碾压态势。这样的对战已经完全颠覆了梁山人物排座次前设定的并且基本遵循的武艺体系。

年画卢俊义、呼延灼
以这些战例评估不同期间不同人物的武艺和对战,往往多有矛盾之处。这似乎也是梁山征田虎、征王庆部分与其他部分并非成于一人之手的佐证之一。
三、呼延灼的结局,既不曾折了“马军五虎将”威名,也不曾辱没祖上名声
需要说明的是,呼延灼领兵征讨梁山展现出的统兵之才,是针对《水浒传》中的情形而言的。
实际上,《水浒传》的优势和特色在于江湖世界的构建和江湖人物的塑造,对于战争的描写则是明显缺陷,行兵对战犹如童稚游戏,且不说与现实中的战争相比违背战争规律,即便与《三国演义》中的战争描写相比也是相差悬殊。《三国演义》中层出不穷的谋略用计更是让《水浒传》中的谋略用计黯然失色。
金圣叹批读《水浒传》时写道:“呼延灼却是出力写得来的,然只是上中人物。”[15]“出力写得来的”的是呼延灼勇猛过人的武艺,以及领兵征讨梁山期间以“连环马”大出风头的故事;“只是上中人物”则源于他的人物形象塑造并无灿烂亮眼之处,是中规中矩的标签式人物。

金圣叹批点《水浒传》
因为《水浒传》中的精彩片段主要集中于前半部分,人物形象塑造也集中于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其他部分故事情节精彩度和人物形象鲜明度大为逊色,且兼呼延灼登场时,《水浒传》已经从讲述个人故事转为描写群体活动,再无像鲁智深、林冲、武松那样性格鲜明而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塑造,呼延灼自然未能逃脱这一规律的制约。
依据《水浒传》中的故事情节推测,无论是呼延灼还是关胜,归附梁山都很难认定是心甘情愿的,他们归附梁山的理由更是颇为牵强的。
呼延灼、关胜等朝廷军官降将对招安诚心拥护,固然是宋江提议在先,他们的出身、经历及入伙前的职位则是赞同招安的关键性因素。
既然梁山不能或不甘永远以“贼寇”自居,招安在客观上就属于应对得体的决策,自然对呼延灼、关胜等朝廷军官降将未便严词谴责。呼延灼、关胜接受招安后确实实现了“尽忠报国”夙愿。
而出身、经历及入伙前的职位对他们处境及结局似乎也不无裨益。梁山征方腊班师还朝后,呼延灼、关胜不仅未遭遇被害身亡之灾,反倒颇受重用——关胜为“大名府正兵马总管”,“在北京大名府总管兵马,甚得军心,众皆钦伏”。呼延灼为“御营兵马指挥使,每日随驾操备”。(第一百回,1296页)虽说众生平等,出身、经历之不同,又岂可轻视?
呼延灼的“御营兵马指挥使”属于皇帝亲卫。关于呼延灼的结局,《水浒传》中写道:“呼延灼……后领大军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阵亡。”(第一百回,1296页)这是比征方腊更加轰轰烈烈的“尽忠报国”。中国古代有“马革裹尸”、“血洒沙场”的慷慨激昂,这是无数军人向往的境界和结局。

连环画《双鞭将呼延灼》
《水浒传》续书《水浒后传》中,金兵侵占河北、河东,形势岌岌可危,徽宗皇帝传位太子赵恒(钦宗皇帝)。钦宗皇帝登基后,命内侍太监梁方平统领呼延灼等十将分守黄河岸口阻遏金兵。
呼延灼同江豹连营扎寨,汪豹暗通金兵,宋军仓促应战,不敌溃败。呼延灼在其子呼延钰及“金枪手”徐宁之子徐晟保护下,并力杀出重围。呼延灼报国无门,追随李应等人在饮马川重新落草。
不久,金兵攻陷京师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及宗室、后宫、贵族及大臣数千人。李应、呼延灼等梁山余人以报国勤王为己任,加入李纲、宗泽为首的抗金阵营,处死祸国殃民的蔡京、童贯、高俅、蔡攸等。
而后迫于形势,他们冲破金兵重围,弃寨出海,前往暹罗国与李俊会合,适逢暹罗国内乱,他们扶助李俊为暹罗国主。宋高宗册封李俊为暹罗王,并封赏群臣,“王进、关胜、呼延灼、李应、栾廷玉 五虎大将军,皆封列候”。[16]

有益堂刊本《说岳全传》
《说岳全传》中依据《水浒传》的内容构想了年迈的呼延灼杀敌阵亡的细节(与《水浒传》中并不一致):“靖康之变”后,侥幸躲过劫难的徽宗皇帝之子康王赵构在朝臣拥立下登基称帝,即为宋高宗。宋金之战期间,宋高宗被金兵统帅兀术(四太子)追杀至海盐县,无人救驾,大将王渊推荐退隐该地多年的呼延灼前来保驾。呼延灼初次出阵便击杀兀术麾下长江王杜充,兀术亲自接战呼延灼。书中写道:
番兵败转去,报与兀术道:“长江王追赶康王,至一城下,被一个老南蛮打死了。”兀术道:“有这等事!”就自带兵来至城下,叫道:“快送康王出来!”高宗正与众臣在城上,见了流泪道:“这就是兀术,拿我二圣的!孤与他不共戴天之仇!”呼延灼道:“圣上不必悲伤,且准备马匹。若臣出去不能取胜,主公可出城去,直奔临安,前投湖广,寻着岳飞,再图恢复。”
说罢,就提鞭上马,冲出城来,大叫:“兀术休逼我主,我来也!”兀术见是一员老将,鹤发童颜,威风凛凛,十分欢悦,便道:“来的老将军何等之人?请留姓名。”呼延灼道:“我乃梁山泊五虎上将呼延灼是也。你快快退兵,饶你性命。不然,叫你死于鞭下。”
兀术道:“我非别人,乃大金国兀术四太子是也。久闻得梁山泊聚义一百八人,胜似同胞,人人威武,个个英雄,某家未信,今见将军,果然名不虚传!但老将军如此忠勇,反被奸臣陷害。某家今日劝你不如降顺某家,即封王位,安享富贵,以乐天年,岂不美哉?”呼延灼大怒道:“我当初同宋公明征伐大辽,鞭下不知打死了多少上将,希罕你这样个把番奴!”
遂举鞭向着兀术面门上打去。兀术举金雀斧架住。两人大战了三十余合。兀术暗想:“他果是英雄。他若少年时,不是他的对手。”二人又战了十余合。呼延灼终究年老,招架不住,回马败走。兀术纵马追来。
呼延灼上了吊桥。不知这吊桥年深日久,不曾换得,木头已朽烂了。呼延灼跑马上桥,来得力重,踏断了桥木,那马前蹄陷将下去,把呼延灼跌下马来。兀术赶上前,就一斧砍死。城上君臣看见,慌慌上马出城,沿着海塘逃走。
那兀术砍死了呼延灼,勒马道:“倒是某家不是了!他在梁山上何等威名,反害在我手。”遂命军士收拾尸首,暂时安葬:“待某家得了天下,另行祭葬便了。”[17]
对于呼延灼的结局,抛开《水浒后传》中“皆封列候”的“大团圆”结局不提,无论是《水浒传》中的“出军杀至淮西阵亡”,还是《说岳全传》中的死于金兀术斧下,都是为国捐躯,且死得甚是壮烈。

《水浒后传》
战死沙场固然令人伤感,作为名将后裔,“马革裹尸”、“尽忠报国”或许才是自身价值最有分量的体现。呼延灼这位名将后裔,梁山的“天威星”,既不曾折了“马军五虎将”威名,也不曾辱没祖上名声。
四、“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名将家史演义是反向反映现实的
中国民间传说及古典白话小说中,最为声名远播、英才辈出的忠良将门是杨家将。呼延家同样是声名远播、英才辈出的忠良将门。“呼家将”与“薛家将”、“杨家将”构成了古典白话小说史上的“三大家将小说”。
即便这些家将小说故事情节粗糙,人物形象单薄,艺术价值不高,却流传广泛、声名颇著。《水浒传》中,“小旋风”柴进为五代后周周世宗柴荣后裔,是“龙子凤孙”的嫡传人物,与高贵门第的密切关系毋庸置疑。
相比之下,《水浒传》中并未过多渲染呼延灼与呼延赞及呼家将之间的密切关系。呼延灼与杨志作为杨家将后人一样,忠良将门只是他们身份和意识的标签,并非展开故事情节的背景,他们也并非主要角色。尽管杨志的家族意识和“封妻荫子”、尽忠报国意愿的强烈是呼延灼难以企及的。
《水浒传》中有梁山征辽故事。辽国兵马被梁山兵马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向宋朝请降。辽国请降时,宋江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辽国使者、丞相褚坚说道:“俺连日攻城,不愁打你这个城池不破。一发斩草除根,免了萌芽再发。看见你城上竖起降旗,以此停兵罢战。两国交锋,自古国家有投降之理。准你投拜纳降,因此按兵不动。容汝赴朝廷请罪献纳。”丞相褚坚承诺道:“奉表称臣,纳降请罪,告赦讲和,求敕退兵罢战,情愿年年进奉,不敢有违。”(第八十九回,1146-1147、1148页)

明崇祯青花呼延灼战扈三娘图莲子罐
真实历史上,宋太宗雍熙三年(986),为收回五代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宋太宗派遣二十万大军北伐,三路大军最初进军顺利,收复不少失地,后因指挥失误,大军败北,收复州县得而复失。
此后宋朝再无收回燕云十六州可能,宋朝对辽国的战略关系也由进攻转为防御,辽国的攻击、夺城、抢掠时有发生,宋朝根本无法除去边患。宋真宗年间,辽国和北宋互有攻守,互有胜败,双方厌战情绪上升,经过一番对抗,签订“澶渊之盟”,两国约为兄弟之国,此后有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
即便如此,宋朝每年需要送辽国岁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年间,在辽国咄咄逼人的挑衅下,为求得边境安宁,每年又增加岁币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而无论是和平期间还是战争期间,辽国长期对宋朝保持着压制性的威胁,也掌握着双方是战是和的主动权。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与《水浒传》中的故事情节完全相反。

倪东坚绘双鞭呼延灼
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8]
人们也常说:“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说法都是有相当道理的。进一步而论,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时,有时是正向反映的,有时却是反向反映的。对于前者,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什么,文学作品就正向反映什么;对于后者,是现实生活中缺少什么,文学作品就反向反映什么。文学作品反向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在民间传说及古典白话小说中有着异常突出的反映。
宋朝经济繁华、文化璀璨、氛围宽容,而又“重文轻武”,以致军事积弱、受制受辱于邻国,屡屡丧失钱物和领土。
长年累月如此,国人对受制受辱于邻国的局面感到憋屈愤懑,对抗击敌国、保家卫国的慷慨事迹心驰神往,称颂追思铁骨铮铮、保家卫国的武将。现实生活无能为力,文学作品就成为寄托怀抱、消解块垒的工具。杨家将和呼家将等家将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流传的。
《杨家将》、《说岳全传》等小说成书于明清时期,却并非原创作品,而是数百年流传的家将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实际上,杨家将、呼家将的故事从北宋时期即开始流传、演变,岳家将的故事从南宋时期即开始流传、演变。

修文堂刊本《杨家将》
民间长期流传、演变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倾向对小说的成书又有着决定性影响。这些小说多有违背历史的创造,甚至完全抛开真实历史,依据一己意愿编排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鲁迅指出:“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19]这些小说正是寄托民间真实情绪的重要载体。
再以岳家将为例。真实历史上,岳飞先后参与、指挥大小战斗数百次。金军南下时,岳飞力主抗金。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收复襄阳六郡。绍兴六年(1136),攻取商州、虢州等地。绍兴十年(1140),金国将领完颜宗弼领兵攻宋,岳飞挥师北伐,收复郑州、洛阳等地,进军朱仙镇。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一意求和,催令岳飞班师,北伐成果得而复失。
后在宋高宗指使下,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诬陷入狱,1142年,以“莫须有”罪名惨遭杀害。岳飞体恤部属,赏罚分明,岳家军军纪严明,能征善战,以至于金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20]的评语。
“(秦桧)杀岳飞於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21]金人自认宋军“将帅中唯岳飞为金人所畏”。[22]

岳飞书《吊古战场文》
《说岳全传》前部分(前六十回),岳飞在母亲严教下长大,师从周侗学艺,文武双全。成年后追随名将宗泽。康王赵构在金陵即位后,岳飞入伍抗金,此后不断南征北讨,很快成为与韩世忠等人齐名的名将。岳飞在朱仙镇大破金兵“连环马”、“铁浮陀”。准备直捣黄龙府时,十二道金牌令岳飞班师还朝,后被秦桧夫妇冤杀于风波亭。
《说岳全传》前部分关于岳飞的故事,有杜撰、有夸大、有变异,却不乏现实的影子,甚至岳飞的功绩在小说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示。
《说岳全传》后部分(后二十回),宋孝宗继位,为岳飞平反昭雪,敕命岳飞次子岳雷挂帅扫北,岳雷统帅众多岳家军老辈英雄和后辈新秀,攻城略地,逼得金国连连败北,不得不归地求和,岳雷完成了其父未竟之志,大宋朝廷也去除了边患。而真实历史上的岳雷,岳飞被捕时年仅十六岁,一度入狱侍父。岳飞被害后,发配岭南,未及等到朝廷为岳飞平反即死于流放之地。与岳云追随父亲南征北战不同,岳雷生平既无赫赫战功,也无重要官职。
如果说《说岳全传》前部分大致符合章学诚评说《三国演义》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23]的说法,《说岳全传》后部分关于岳雷的故事则是毫无依据的凭空杜撰。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许多历史类影视作品树立的创作原则,力争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完美结合。历史小说创作似乎也应以此为准绳。故此,历史小说创作需要摆脱真实历史的束缚,又不能完全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家将小说虽然涉及诸多历史人物,甚至以历史人物作为主角,却属于英雄传奇小说。

邮票《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以笔者浅见,这些小说不值得夸赞的地方不在于有大量虚构的故事情节,而在于故事情节往往在体现“尽忠报国”、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等光辉理念的同时,还体现着一种意淫过深、自我陶醉的理念,即:与现实生活完全背道而驰,过分贬低敌国、轻易战败敌国,大显天朝上国声威。
以两部有所关联的小说为例。《三国演义》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都是出于虚构: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等。而《三国演义》的故事脉络并不违背真实历史:战乱纷纷,群雄逐鹿,魏蜀吴三足鼎立,最终统一于晋。为尊重真实历史,《三国演义》并不肆意编造故事情节,以至于关羽败走麦城,诸葛回天乏力。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的故事情节与前面相比更是索然乏味,甚至让人憋屈愤懑。
民国时期周大荒著有《反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立场尤甚于《三国演义》,故事情节编排更是趋于极端。
从徐庶进曹营开始改写故事:徐庶未进曹营,庞统未死于落凤坡,刘备有孔明、庞统和徐庶三大军师运筹帷幄,又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等五虎上将,并加大赵云与马超的戏分,蜀国东征孙吴,北伐曹魏,吕蒙偷袭荆州并未成功,魏延偷渡子午谷成功,袭取长安,最终攻陷魏国首都许昌,魏国皇帝逃往北方,蜀国统一天下。

孙忠会绘呼延灼
较之《三国演义》可以说是“零分实事,十分虚构”。故事情节如此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与历史小说绝无关涉,反倒犹如一部借用历史人物名字的架空小说。这样的故事情节体现的理念也与家将小说如出一辙,似乎正是回避现实生活、徒逞口舌之快情绪的产物。
注释:
[1]本文所引《水浒传》文字,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水浒传》。
[2]全名《杨家府演义》、《说呼全传》。
[3]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21页。
[4]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43页。
[5]有趣的是,在以杀戮梁山人物为能事的《结水浒传》中,作者俞万春又将呼延绰确定为呼延灼堂兄弟。
[6]黄永年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第1998页。
[7]曾枣庄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五代史》(全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第275页。
[8]倪其心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第6368页。
[9]倪其心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第6368页。
[10]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222页。
[11]施耐庵著、郭皓政辑评:《百家精评本水浒传》(下),崇文书局,2019,第830页。
[12]施耐庵著、郭皓政辑评:《百家精评本水浒传》(下),崇文书局,2019,第850页。
[13]施耐庵著、郭皓政辑评:《百家精评本水浒传》(下),崇文书局,2019,第897页。
[14]施耐庵著、郭皓政辑评:《百家精评本水浒传》(下),崇文书局,2019,第902页。
[15]施耐庵著、金圣叹批评:《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上),岳麓书社,2006,第3页。
[16]陈忱:《水浒后传》,凤凰出版社,2017,第306页。
[17]钱彩:《说岳全传》,华文出版社,2018,第276页。
[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60、861页。
[19]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51页。
[20]倪其心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十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第8082页。
[21]陆游撰:《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第4页。
[22]毕沅:《续资治通鉴》(七),中华书局,1957,第3302页。
[23]转引自郑增乐:《“真实”及“正统”论:毛本<三国>的文体焦虑》,《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即便《三国演义》中有大量虚构的故事情节,鲁迅还是认为,《三国演义》作为小说是“实多虚少”。(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33页)。鲁迅似乎有认为其过于拘泥史实之意。他的意见也不是孤立的。胡适认为:“《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胡适:《胡适文集》(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91页)。从《三国演义》全书而论,各部分故事情节的虚实比重确实是相当不均衡的。由此可见,即便对历史小说创作需要虚实结合的原则争议较少,对于不同历史小说的虚、实多少及成败评判,还是意见纷纭的。

打累一个又换一个妥妥的车轮战[哈哈笑],什么好汉?是实打实的无耻之徒[得瑟][好生气][好生气]